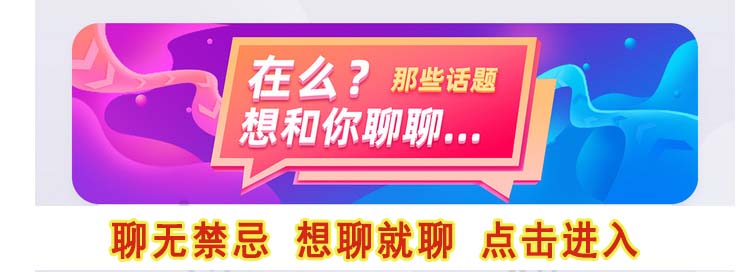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有两个外婆!
几十年前,亲外公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执教的收入维持家庭开支捉襟见肘。其时,妈妈上面,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的经济更雪上加霜,无力抚养的外公只好把他的这第三个孩子放在路边,躲藏在一边等待,直至等到了一对衣着不俗的男女高兴地抱走孩子后才放心回去。而这两位,就是妈妈的养父母-----也是我的外公外婆,居住在小镇的他和她,婚后三年都等不来一儿半女,这次来县城是回娘家探亲,意外看到路边哇哇大哭的女婴,惊喜之余,动了收养的念头。
妈妈的养父(外公)我没得见过,他在我没出生时就去世了,听妈妈说,他是到县城公干时,邂逅了相貌出众、性子温和的外婆,两情相悦后便是喜结连理,郎才女貌,一时羡煞旁人。在抱养妈妈后的第三年,外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我的舅舅,一家子其乐融融。
可惜这幸福的日子不长久,在妈妈8岁那年,“文革”开始了,外公被赶下台,好在他平日为人良善,并没有被批斗,但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工作,外公只能回到农村老家务农,可怜从来没有干过重活的外婆,要下田耕种,上山砍柴,翻山挑水,喂养家禽,生活一下子水深火热起来。
四年后,命运再一次向外婆伸出了魔掌——外公得了重病不治而亡。不到13岁的妈妈辍学回来,两个曾经被呵护到无微不至的大小女人,不得不辛苦地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
妈妈和外婆感情很好,一直陪着她在农村务农,直至25岁才嫁到邻村。在我一岁那年,外婆在合浦的娘家人,给她介绍了一个木工做老伴,让她从小镇得以搬回了县城,这位木工外公经济上也不宽裕,一直和几家人共同租住合浦常见的巷子里。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里,外婆和妈妈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他,我只在12岁时见过他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那是在妈妈第一次带着我从小镇到合浦探望外婆的时候。
狭长的小巷,凹凸不平的地面,推开笨重的木门,是长长的过道,夏日的正午,外面艳阳高照,里面的过道却朦胧昏暗。宽约三米的过道左边放置着各种杂物,甚至还有一个垂着蚊帐的架床!右边余半米宽供人行走,最里面才是5间房子,三家人合租。
我在外婆房间坐不住,一个人到外面瞎逛,玩累了回来,走到过道中间时,一边放置的架床里面突然传出声声痛苦的呻吟,我虽然被吓了一跳,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是抻出手揭开半幅床帘,入眼的那一幕,凄惨得让我今生难忘:床中间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弓起的左脚膝盖处血肉模糊,像刚被狗咬过一样参差不齐,血,不间断地从那里一滴滴往下掉,伤口下面是一截裸露的光秃白骨,流转着让人毛骨悚然的震撼。
老人大大的眼睛里饱含着痛出来的泪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被吓到了,恐惧让我什么反应也没有,呆呆地和他对望。不知多久,我才回过神回到妈妈面前,跟她诉说刚才的所见,妈妈跟我说这是外公,他得的病治不好,要截肢,不然全身的肉会逐渐被病菌吃掉,但是2万块的手术费家里拿不出。只好让他一天天痛着。我无法想象这世上竟有如此霸道可怕的病,太吓人了。外婆的再嫁竟然遭遇了如此不幸的事!我们探完亲回去不到两个月,这位外公便去世了。外婆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0年。
生活的艰辛把外婆变得沉默寡言,再不复往日的神采,她来我们家时,帮忙干完活后便是长时间的坐在椅子上发呆,灰白的长发常年盘成绾,前面总有两缕不听话的挣脱出来,随风飘动在白皙姣好的脸庞上,仿佛在慰藉她伤痕累累的内心。虽然和这位外婆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每次看到她,心里都是满满的温情。我们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我只喜欢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
舅舅娶妻生女后,外婆一直和他们在中心市场后面租房住,半辈子做建筑工的舅舅,一个人养育着妻儿和老妈,过重的负担硬生生地把他从白净英俊的青年,熬成了满脸沧桑的失意男人。生活的不如意让他容易情绪失控,收工回来看那个都不顺眼,家里人经常被他大声呵斥,屋里的空气沉闷压抑。
每当舅舅说那些过分的话时,外婆唯一的反应只是把头一低再低,像个做错事的小孩,眼睛里一片死寂。
人老了受嫌弃,都说养儿为防老,事实上又有几个人真正能做到尽善尽美?年迈病痛缠身的外婆,白天坚持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后,就是静静地坐着,陪着她的,只有满屋没有生命的杂物。
家里唯一的电视在舅舅住的阁楼上,外婆从来不敢上去看过,晚上大家坐在阁楼看电视时,外婆识趣地回到了自己房间关上门,让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我无数次的把自己设想成外婆,想如果我是她,这样的生活开心吗?好过吗?想要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独自到北海打工的头两年,经济最是窘迫,有限的收入除去房租和一天两餐,所剩无几。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了我和外婆相见的步伐,我怕晒,怕脏,怕坐车,但我更怕想而不得的情感折磨,于是一月一次到合浦探望外婆,成了我生活里雷打不动的习惯。
一次,我到时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她说舅舅和舅妈去做工了,两个表妹在学校中午不回来。我看到饭桌上只有一个残留着菜汁的空碟子。外婆说:“你还没有吃午饭吧,我去隔壁借菜给你吃。”
“轰”我心口那道叫悲伤的闸门,被外婆的这声“借菜”炸得灰飞烟灭,汹涌而至的悲愤让我差点站不稳,闻所未闻的“借菜”两个字,能折射出多少心酸,我的心就有多堵。外婆,我可怜的外婆,没吃午餐的是你啊,而这显然不是一回两回的了!
摸出干扁的钱包,我出去买了外婆喜欢的烧鸭和青菜,回来时外婆已煮好饭,婆孙俩挨着吃了一顿温馨的午餐。饭后外婆迈着蹒跚的步伐,跟往常一样,坚持要送我到路口,我一路催她回去,她不听,我走出了很远,回过头,还能看到外婆站在那里,费力地伸直腰,不舍地凝望着我,历尽了人生酸苦的目光流出温暖的情感,似雨露一样滋润我干涩的心田,湿润了我的眼眶。
2013年,经常往返合浦的妈妈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彼时亲外公外婆经济条件已大大改善,一边领着退休金,一边收着铺租。每次见到我们兄妹,都塞钱给我们。但我还是觉得和那位从小处到大的外婆亲一些。
不久后,我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结束了拮据尴尬的生活,走进了另一个家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马上跟舅舅商量要把外婆接过来暂住,舅舅一口拒绝了,说外婆太老了,坐不了车,经不起折腾。我只好无奈放弃,心里却知道舅舅是放心不下把外婆交给我这个没经验的小鬼照看,外婆应该也不肯来,毕竟合浦有她血脉的蔓延,满满的都是她的牵挂。
前年7月的一个平常日子,89岁高龄的外婆悄无声息地在睡梦中去了,结束了她坎坷的一生。
我心里紧绷着的那根弦,断了。
一直以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婆如此的牵动我心?也许是她从来不与人为害的品性,也许是她安静的忍让,也许是她隐藏起来的痛楚,激发了我内心的怜悯,吸引我靠近。
就在去年,舅舅终于熬出了头,承包了几个工程,经济上有了质的飞跃,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楼房。舅舅说起自己苦命的亲娘时,满脸的悔意,恨自己当初没能力好好孝顺她,到了现在,子欲养时,亲,却不在了!徒留下一地的懊恼。已仙游的外婆,未呈儿孙福的外婆,游魂于千里的外婆,我们该怎么把思念传递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