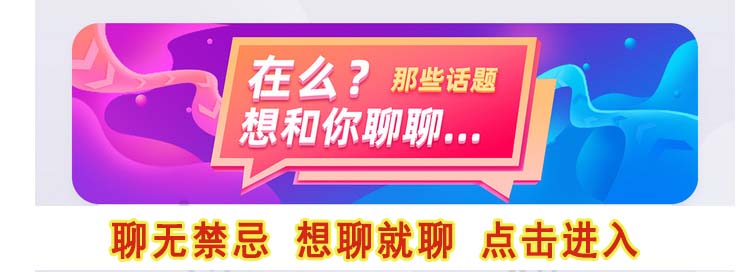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胡适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中国大陆,北京政府曾对胡适进行过广泛的批判,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因此蒙受过不明之冤。
胡适追随国民党,摒弃了共产党,这是胡适必然要走的道路。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饱受了英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润,而这些思想都与共产党及其暴力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相比之下,鲁迅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我一个也不宽恕”时,与共产党暴力革命有着某些逻辑上的暗合。鲁迅的思想,注定了他与共产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此被毛泽东封了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胡适说过,“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暴力革命可能声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本来就是不宽容的态度。暴力革命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暴力革命取得成功时,必然对反对党采用暴力镇压反对党。在胡适看来,暴力革命必然带来“反民主的集体专制。”
表面上看起来,胡适好象不喜欢共产党。事实上,胡适反对的都是不容忍态度——谁要用暴力推翻政权,胡适就会为该政权说话,即使该政权有很多问题。如此一来,胡适给人有“保守”的感觉。胡适不赞成暴力革命,也就成为了革命者心目中的“反革命”。对于胡适而言,变革不是一夜间的“批发”,而是点点滴滴的累进变化。我们可从中看出,胡适的思想中还有很深的“进化论”的烙印。
在胡适看来,国民党也搞一党专制,但不承认一党专制是最终形式,它只是过渡到宪政的准备时期,这是孙中山早就认定了的观点。因此,国民党只是威权政治,还不是极权政治。不像极权政治,威权政治的触角不会向国家和社会无限延伸,也不会用意识形态来“结扎”民众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适办过《新月》和《独立评论》杂志,虽然被查封关掉过,但还可以再办。很明显,在威权政治下,思想和言论还能有一点空间。
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开始使用“极权”这一概念,并将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胡适对俄国的“十月革命”颇有微辞,认为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看来,胡适不喜欢共产党也就再所难勉了。不过,从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30年内,以“人民专政”的口号,对人民进行了专政治。这证明了胡适的思想并没有错,也证明了他到台湾是正确的选择,否则,他留在大陆的结果只会是瘐毙而亡。
坦率地说,从今天来看,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刻,却富含着逻辑与智慧。前面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宽容的,不宽容就是反民主。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它必然是采用暴力形式来镇压反对者。尽管它会打着“民主”的旗帜,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极权政治。瞧瞧,多么简单的逻辑,它甚至是常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正是常识而已。
我们知道,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经济秩序》等著述中,哈耶克详尽论述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胡适更早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广泛接受他的思想。
我也想到了孔庆东。这位号称“北方醉侠”的北大副教授贬抑胡适,说他“没有多少传世的话”,只作了《兰花草》那首校园歌曲的歌词。当然,孔是研究鲁迅的,视野不一定开阔,情感上比较偏袒鲁迅,这好象也可以理解。其实,胡适有很多名言,我比较喜欢的有: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异乎我者未必即是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我原谅了孔庆东,开始赞赏李敖。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捐献了二十万元,为胡适做了一座铜像,并置于北大校园之中。胡适这位北大的老校长,终于在21世纪回到了北大的怀抱。
历史开始卸下重负。在真理开始敞亮之际,胡适也必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
胡适追随国民党,摒弃了共产党,这是胡适必然要走的道路。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饱受了英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润,而这些思想都与共产党及其暴力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相比之下,鲁迅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我一个也不宽恕”时,与共产党暴力革命有着某些逻辑上的暗合。鲁迅的思想,注定了他与共产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此被毛泽东封了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胡适说过,“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暴力革命可能声称自己是民主,甚至是真正的民主,但它本来就是不宽容的态度。暴力革命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暴力革命取得成功时,必然对反对党采用暴力镇压反对党。在胡适看来,暴力革命必然带来“反民主的集体专制。”
表面上看起来,胡适好象不喜欢共产党。事实上,胡适反对的都是不容忍态度——谁要用暴力推翻政权,胡适就会为该政权说话,即使该政权有很多问题。如此一来,胡适给人有“保守”的感觉。胡适不赞成暴力革命,也就成为了革命者心目中的“反革命”。对于胡适而言,变革不是一夜间的“批发”,而是点点滴滴的累进变化。我们可从中看出,胡适的思想中还有很深的“进化论”的烙印。
在胡适看来,国民党也搞一党专制,但不承认一党专制是最终形式,它只是过渡到宪政的准备时期,这是孙中山早就认定了的观点。因此,国民党只是威权政治,还不是极权政治。不像极权政治,威权政治的触角不会向国家和社会无限延伸,也不会用意识形态来“结扎”民众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适办过《新月》和《独立评论》杂志,虽然被查封关掉过,但还可以再办。很明显,在威权政治下,思想和言论还能有一点空间。
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开始使用“极权”这一概念,并将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胡适对俄国的“十月革命”颇有微辞,认为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看来,胡适不喜欢共产党也就再所难勉了。不过,从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30年内,以“人民专政”的口号,对人民进行了专政治。这证明了胡适的思想并没有错,也证明了他到台湾是正确的选择,否则,他留在大陆的结果只会是瘐毙而亡。
坦率地说,从今天来看,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刻,却富含着逻辑与智慧。前面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宽容的,不宽容就是反民主。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它必然是采用暴力形式来镇压反对者。尽管它会打着“民主”的旗帜,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极权政治。瞧瞧,多么简单的逻辑,它甚至是常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正是常识而已。
我们知道,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经济秩序》等著述中,哈耶克详尽论述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胡适更早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广泛接受他的思想。
我也想到了孔庆东。这位号称“北方醉侠”的北大副教授贬抑胡适,说他“没有多少传世的话”,只作了《兰花草》那首校园歌曲的歌词。当然,孔是研究鲁迅的,视野不一定开阔,情感上比较偏袒鲁迅,这好象也可以理解。其实,胡适有很多名言,我比较喜欢的有: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异乎我者未必即是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我原谅了孔庆东,开始赞赏李敖。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捐献了二十万元,为胡适做了一座铜像,并置于北大校园之中。胡适这位北大的老校长,终于在21世纪回到了北大的怀抱。
历史开始卸下重负。在真理开始敞亮之际,胡适也必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