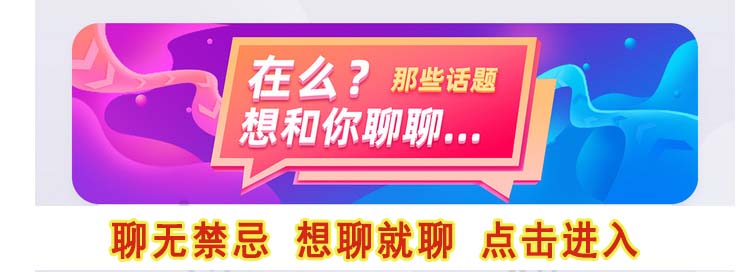在湘中名山紫云峰脚下,有一村名叫寒坡村。寒坡村有个寒坡坳,十来户人家居住在这里。作为高寒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寒坡坳的名头似乎并不那么响亮。可是如果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那么,小小的寒坡坳在方圆数十里绝对算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时候密荷公路还没有修通,荷叶的人们若要上县城,寒坡坳是必经之地。可以说,寒坡坳是荷叶西去的门户。因此,寒坡坳附近很早就有了商铺和客栈。
从寒坡坳沿河而下,不过两公里便到达藁枪仑。藁枪仑是一条笔陡的石板路,从会龙桥到张沽塘,长约一公里,垂直高度近百米。藁枪仑因何得名,现已无从考证,今姑且从字面来作个猜测。藁枪者,原是一种用稻草编的垫床用具,相当于草席。由此想来,或许因此地农业相对发达,稻草极丰,当地人民竞相编织藁枪,这里竟逐渐成为了藁枪生产基地。又或许因藁枪每隔一段就有一突出部分,望之如一级级阶梯,莫非藁枪仑竟是因形而名?不管藁枪仑得名何由,总之都与藁枪有关,这应该是错不了的了。
站在“仑”下仰望,石梯层层,愈升愈高,让人几疑可以沿此踏上云头,直登仙界。站在“仑”上下视,如临深渊,望之胆寒。一条小河顺着山势,奔流不息,拐过几个山坳,倏忽不见。远处,山峰重重叠叠,伸向遥远的天边。藁枪仑附近,一眼望过去尽是梯田。在“人定胜天”的年代,劳动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激情。他们只知道劳累的是身子,填饱的是肚子。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只是农民,他们还是诗人、画家。那一层层的梯田,不就是一行行整齐的诗句吗?看吧,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那流动的线条,那震撼的层次,不正是一幅最美的巨幅画卷吗?
站在藁枪仑上,多少故事在回想。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满清政权风雨飘摇。当此乱世,一对荷叶籍兄弟横空出世,硬是将处于悬崖边上的清王朝生生地拉了回来。他们,就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1864年,曾氏兄弟打开南京发洋财,功高盖世,位极人臣。随后,曾国荃在今大坪村建大夫第。却说有一次,曾国荃由京城至省城再经永丰归家,走的就是藁枪仑这一条路。曾国荃深知此处路狭难行,过了永丰,便舍了车驾,骑马而行。行至恒福堂路段,道路益窄,仅容一马通过,两旁高山直上云天,路边是悬崖峭壁,下临万丈深渊。饶是曾国荃身经百战,也不由暗暗心惊。他下了马,小心翼翼地牵马前行。突然,骏马一失足,滚下了深涧,那凄厉的哀鸣,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受此惊吓,曾国荃深感家乡人民行路艰难,于是对原路进行了维修,并把张沽塘至会龙桥的一段最险要的路铺上了石板,这就是今藁枪仑了。
藁枪仑,你可曾记得往来于永丰的匆匆过客?想当年,一群赤膊的汉子,挑着担子,踏着清晨的露水出发,伴着西下的夕阳归来。肩上的重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在这群汉子当中,有一个人特别与众不同。当别人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之时,他依然气定神闲、健步如飞。他肩上的担子,是所有人当中最重的一百五十斤!尤其令人称奇的是,他中途根本不需要喝水,也从不用歇肩,他的口袋里有一种特殊的干粮——砂盐。每走一段,他就掏几粒放到口里,“咯嘣”一声吃下去,顿时精神倍增。寒坡距永丰二十余公里,他朝发寒坡,午至永丰,及归家,亦不过下午四时,常人虽空手徒步亦莫能及也。如今,斯人已去,“铁汉”的故事仍然流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藁枪仑附近的农田大多已荒芜。与此同时,寒坡坳经石牛至永丰的公路已全线贯通并硬化,一班客车往返于两地之间,古老的藁枪仑再不复当年的繁华。近年来,一批有识之士光顾了藁枪仑,他们强烈呼吁重修藁枪仑,并重新开垦附近梯田,把寒坡梯田打造成国藩故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若果如此,则藁枪仑有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