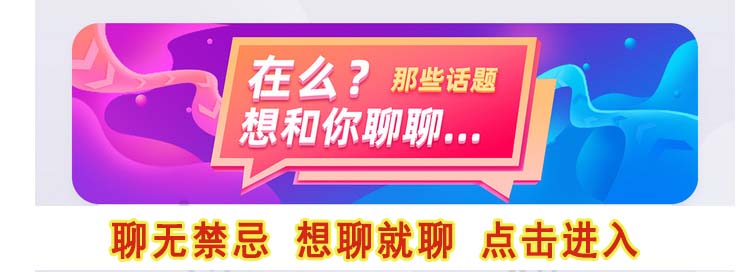祁东人凡有红白喜事,皆好摆“十到”酒。而论一场“十到”酒的丰盛与否,是与其中的一道菜有着莫大关系的。
二三十年前,在酒席桌上常会听到有人对菜肴进行点评:“瞧这盘肉,才二斤吧,也太会打算盘了。”“古才讲礼性呢,盘肉出起雷钵大。”其实,无论是盘肉的大和小,都是与家里的经济状况有关,一年辛辛苦苦到头还要欠钱欠米的人家,盘肉小一点,也无可厚非。
可以说,昔年的农家,盘肉就是一个家庭的晴雨表。透过它,很能看出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当然还可看出其主人的量气大小。其实,说到量气,那些在酒席上作月旦评者,也未必就肯定够大。农村吃席的菜是要圴分的,当一块盘肉切成八小块端上桌时,还是有不少的人会鼓起眼睛瞪着的,生怕分菜者将一块份量不够八分之一的给了自己。
我喜欢吃盘肉菜,特别是肥的那种,切薄片小火炸出油,使其微微泛黄,卷成耳子状,加红辣椒、芹菜,再佐以蒜子、姜丝,那个香、辣、甜啊,就全都汇集到一锅了。
还有一种吃法,更简单更直接。将肥的盘肉切成一指宽,置于碗里,加豆豉,煮饭时在饭面蒸,出锅后再放蒜葱,这样吃起来就是一个甜和软。一块肥肉,看着在碗里一大块,用筷子就是夹不起来。不是滑,而是太糜烂,筷子一下就一分为二,幸好有皮连着,才会巍颤颤地夹入口中。这样的盘肉我虽然爱吃,但也只是吃一二点而已,再多就有腻的感觉了,只能放筷。
要想盘肉不这样腻,就只有用榨菜了。一块盘肉,一层榨菜,整齐码于碗中放锅里开蒸,因为盘肉上的油被榨菜吸去不少,自然地腻味也就少了许多。这样的榨菜盘肉,吃起来不仅甜,而且更香。就是榨菜的味道,也提升了几个档次。
我的父亲是乡村厨师,每逢村人摆“十到”酒,盘肉是必备之菜,所以做盘肉是十分理手的。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过年,家里是肯定会做盘肉的。自家杀了猪,父亲先砍下四个猪腿子肉,还要砍一二个猪背脊肉,每个三四斤,反复用刀打干净了,横竖两道稻草扎起来备用。用荷叶大锅盛一锅水,加入桂皮、八角之类香料,再将猪肉冷水入锅,大火烧开。锅水会冒出许多泡沫,就用捞蔸反复捞出,待得捞净,猪肉也熟透了,这时就要用到酱油了。用盘肉钩子钩出,手滔酱油在猪皮上面反复摸擦,再将之入锅去煮。这样摸擦酱油需要三四次左右,猪肉的皮一次比一次变得酱红,而且皱如豆皮,用一根筷子轻轻一摔,差不多没顶,这时的猪肉就得改称盘肉了。
其实,盘肉还有另一种叫法。在广东的时候,有次我去一朋友家吃饭,他就做了盘肉。然而,他一家却称之为东坡肉。我们虽同属祁东西区人,但我的家乡石亭子却与他的步云桥隔了三十来公里,本就在语音上有别,对某物的称呼有异也就不奇怪了。此前,我曾在书本上知道有道名菜叫东坡肉,因为是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所创,便总是觉得是件非常遥远的事。哪曾想,这东坡肉却是我嘴里常吃之物呢。
东坡肉,因为粘了名人的气,一直以来,在我的意念中都是高大上的,这一下就成了寻常之物,倒让我有点诧异了。不过细想之下,我又释然。东坡肉是上了菜谱的名菜,而我的盘肉菜仅仅只是盘踞一域而已,不,甚至连整个祁东都未能通吃呢,这下两者联姻,岂不是盘肉粘了东坡肉的光?有了一身名菜的光环!
我又想,世上许多的事物都由劳动人民创造,自然地撞脸的东西也必不会少,只是由于各地风俗的差异,便有了不同的称呼。也许祁东盘肉更早于东坡肉出世呢,但因了苏东坡的大名,所以就被后来居上,反而更加声名远播了,而祁东盘肉只能籍籍无名,委屈万分。
由此可见,任何事物都是怕“巷子深”的,不单单仅是好酒。其实,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广告效应了,难怪在当今社会,广告成了众多企业抢占商界高地的必备神器。而名人能成广告界的娇子,似乎又可从苏东坡处溯源了。不过,苏东坡毕竟有亘古旷今的词才,更重要的是,他还创造了以其字号命名的一道名菜,又岂是浪得虚名之辈所比的?
如今的所谓明星打个广告,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甚至是千万之巨。假如东坡先生尚在世,恐怕非活活气死不可。
老彭素来不喜随大流,更因身为祁东人之故,所以我也要气苏东坡一次:偏不叫东坡肉,就写祁东盘肉,岂奈我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