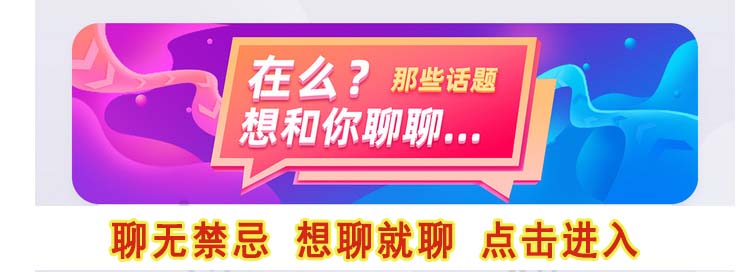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们一行人穿过一座废弃已久的建筑物,从断壁残垣的面目中,我能依稀的觉出这里曾经是一座欧式教堂,虽已破败仍不失肃穆庄严,让人觉得身上一阵阵的寒,我们艰难的穿过了迷宫般的砖墙,像是穿越了一段久远的时空隧道一般,刚才我还觉得这废墟仿佛怎么也走不完,忽然的眼前就豁然开朗了,我们已走出了那些碎乱的砖瓦砾充塞的通道,眼前已然是平阔的美景。
一畦畦的水田罗列,池畔种着垂柳的水塘,可是为什么我从那些低垂的柳叶上,看不出丝毫初春乍绿的欣喜,那柳叶全都泛着深青色的光,只让人觉得异样的恐怖,难道我弄错了?现在还不是春天?可分明两岸还有夹杂而生的桃花,正盛开得艳之灼灼啊。
我正欲问询与我同游之人时,却发觉周围全是陌生的脸孔,便只得住了口。我如何会与这些陌生人同伴同游此地?这是那儿?我怎么全然想不起来了?
我带着疑惑的心尾随一行人继续前行,原本我们是在田野间的阡陌行进的,可是走着走着田埂就完全消隐在水中无路可走了。我们攀上一条绵延数里的河岸,此处桃花更盛,岸上水中全是满目灼灼开得异常妖艳的桃花,那桃花依旧是粉色的,只是粉得异常的光华灿烂,实是我平生未曾见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那种美?如果那算是一种美的话,也是一种妖异的美吧!
这异样的景色让我更加怀疑季节是否真的停在春天,忽然我整个的身体飘浮在了水面上,原来的河岸也消隐不见了,我不断的漂浮着前行,同行的人也不知何时消匿了影踪,只见空气里多了许多精致又模糊的面孔,如我一般来回的漂浮着:闪着幽灵样的人影、满脸邪恶之气的孩童、一队庄严之下隐着哀伤的士兵……他们都从头至尾的沉默着;一切事物都仿佛是漂在空中,且还不自觉的模糊的蠢动着,他们无一例外的,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好像这些人都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好像他们都看不到我,而我只是重叠在他们的世界,窥见了他们的生活而已!
难道?难道这里是……
我仍然不自觉的向前飘移着,我下意识的在寻找,虽然心里并没有目标,我想找到一些关于我这些猜测的证据。从宽阔的路上到初砌的阡陌泥埂上、再从水里漂到岸上,又从高处到平阔、从淡雾缭绕的清晨到落日溶金的黄昏,流光就在转瞬间飘忽了千百回,但我始终没有找到证明自己身在何处的证据!我开始一味的觉得,这一条路永远没有尽头,只觉得一路走来越来越沉重。
突然,我的耳膜被什么声音强列的刺激了,一个寒颤之后我睁开眼,原来是室友小王在叫我,提醒我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
呵,亏得她叫醒我,要不然今天我还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了
生命
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家人说起,我是在四人民医院出生的,而且生得险象环生,差点就小命不保。可能是为了让我懂得生命诚可贵的道理,从小家人就时常向我灌输,关于我生命诞生时的种种,家人把我出生的医院说成我的“老家”,我想这应该也是善良的人们,对于生命感恩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要不是医院的医生把我救活,我就真正是一出生就要回老家(死亡)了,可那时我还不完全的明白“老家”的意义?只是,听他们老是说起,就理所应当的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出处,因此每回生气时,我就吵嚷着我要回老家,并且心底对那个叫着“医院”的地方,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
这大抵都是些童言无忌的往事,会像我一样,把医院当成好出处的人恐怕不多,更惶论对其生出好感,这样奇异的情绪,一直维持到我真正了解到医院,和懂得家人的苦心后,才算是纠正了过来。
巧合的是,我的那个“老家”不仅鉴证了我生命的起程,十多年后又是在那里,我陪伴母亲走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而我与“老家”的缘份还远不止如此,工作后我的工作单位,竟然和四人民医院近在咫尺,我办公室的窗就正对着它的大门而开。
我不知道那一间病房,是二十多年前我来这个世界时的起点?我只是断断续续的听家人说起,当年我出生时的情景,母亲怀着我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一直处在昏迷不醒的状态,医生告诉爸爸,若再任其发展,大、小两个人都有性命之忧,那时的我在母亲的腹中尚未足月。
在那种危急的情形下,父亲当然是要力保大人的,那时候还没有剖宫产,我是被引产下来的,我出生后妈妈仍旧昏迷了多日才醒,并在昏迷中咬坏了自己的舌头,我原本是没有多少生存下的希望的,我的出生只是为了挽救母亲的性命。
我出生后一直像母亲一样昏睡,三天后医生见我还有气息,就倒拽着我狠拍了几掌,这一拍之下我才缓缓的醒过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声啼哭。
据父亲回忆说,那时家人忙于照料母亲,我是交给同病房的病友家属照料的,也许是邻床的那位可敬的家属奶奶的昔心照顾,也或者是我命不该绝,总之我是颇为顽强的活了过来。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又阴差阳错的到了紧挨着这间医院的这个公司里工作,我想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吧!让医院时时提醒我,记得感激生命的可贵!
我出生在这医院时的情景,我是无从知晓的,但十年前,母亲在这间医院的最后一程,我却是记得清楚的。当时,母亲患了脑溢血,像我出生时一样,她又陷入昏迷,医生说唯有手术才有可能挽救她的性命,但成功的几率很低,意即劝父亲放弃手术,免得人财两失。
父亲苦思一夜之后,还是决定动手术,请来的理发师剃光了母亲珍爱多年的长发后,医生在母亲的额头处开了一个小洞,吸出了里面的淤血,手术成功了。
但母亲术后一直昏迷不醒,并且开始发高烧,我一直不停的往医院外的小卖部跑,去买替母亲做冰敷的冰袋,但她的高烧始终不退,终于,曾经挽救过她一次并给了我生命的这间医院,没能再次留住她,。
工作的间隙,我时常踱到了医院的外墙角,现在面对着我的“老家”,我却丝毫也觉察不出它的熟悉来,只感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苍老,我刻意的留意了一下,被我踩在脚下的松软黄土,想看看是不是有翻动过的痕迹。
据说这里是这家医院里新生夭折儿的“墓地”,我的叔叔们当初也曾经为我在此预留了一块,但我终究是没有能用上。我没能发现想像中的墓地,所以也无法证实“墓地”说的真实性,也或许曾经真的有过吧,但那又怎样了,既便是短暂、幼小的生命,仍然是有归宿的,他们不是和其他生命一样,归于尘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