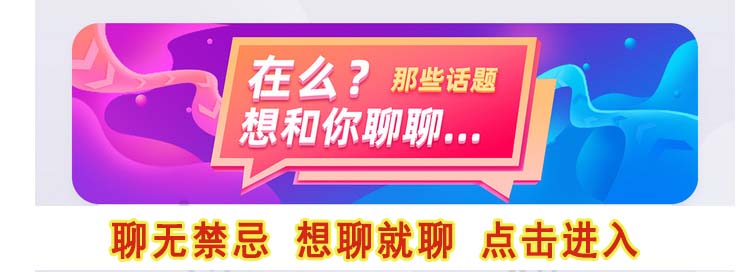因为经文写在贝叶棕的叶片上,人们便把这些经文叫做贝叶经。
我是从电视栏目中了解到的。贝叶棕寿命六十年。但它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也要六十年,结完果后他便死去了。贝叶棕还有一些令人不解的特性:一旦贝叶棕树长成,每年人们都要砍去它三片两片叶子,否则它的寿命就会缩短;如果想起它用到它时就砍,想不起用不到时就把它丢在一旁,它也会早早地死去。
贝叶十分阔大,一人多长、展臂之宽,和芭蕉的叶片很相似。但贝叶棕的叶片是由几十条、上百条一扎宽的叶带组成的。傣家的老人将它采回来放在淘米水里煮,煮时加入酸豆荚,晾干后即可使用了。
经过这样处理后的贝叶,可以保存千年不朽不蛀。
今年三月我得到一尊坐持观音神像,此像五十公分高,为瓷质,素手素面、神态安详;佛体着豆青袈裟,看了说明收藏证书知道这是龙泉厂高级工艺美术师董炳华的作品,非常喜欢。
“佛自西方来”,我将它安置在客厅西壁的花梨木柜上,使她面东而坐;佛座则选用了一块乌江石。此石冰清玉洁,倒立过来上大下小,正好将佛像安放在上面。
第一个见到佛像的人是枫。那日我约她来家饮茶,她来了,进得门来,笑笑地,说:“我换鞋吧!”说着话,不经意的一扭头见了这尊佛像,她便霜打似的噤了声,神情立时庄重起来。她立在佛像前,毕恭毕敬地,从香匣内取出檀香来点着,摇灭,插入炉内;然后双手合十,垂了眼睑,许了心愿才落座。
我问:“你,信佛吗?”
她点着头,复原了笑笑的神情,说:“信。我要的是供奉的过程,佛是神,若按马列主义的说法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上帝就是我们自己!但我觉着佛可以让人把心静下来,对吧?”
我一边给她泡茶,一边大声说着话,这样显得人多。我说:“宗教本来就是人类创造的。宗教的本意是劝善。你听了信了而且行了善了,死后可上天堂,天高九重;若不信,还作了恶那就下地狱,地狱可是十八层啊!”
她接过话去,轻松的说;“胡萝卜加大棒子。你听话,好好干活,年底给你批条红绸被面子,还给挽朵花儿;调皮捣蛋,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那就给你批条麻绳,挽五花!”
她的话使我十分诧异,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文革中的事?那时你才多大?”
她没回答我,只说“我知道的”便把话题引到饮茶上了。饮茶,她也是内行。
枫到我家,这是第一次。尽管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楼挨着楼,相距不过百米;尽管我与她认识已经十多年,但我们很少联系。
我端详着她,她还是老样子,十五年前什么样儿现在还什么样儿。还是那副装扮:上衣紧身,裙摆宽大;一张小脸不涂不抹,衬在云丝间,极富书香气质。
十五年前,她在交大南门外开片玉器店。我从那儿过,走进去认识的她。记得离开时竟然不知道她卖的是青海玉还是和田玉,只是问自己:这是商人吗?她哪儿像个商人啊!
更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她说她是本地人,是土生土长的“兵马俑”!
秦人彪勇,声如狮吼。女人长相多少带点胡人的特征。我便想,什么时候见了一定要问她:你父亲是江苏人吧?如果不是江苏、那他一定是外省外地的;要不你母亲是上海人、重庆人?
现在枫来了,就坐在我的一侧,我们谈着关于玉的事,倒把该问的事忘了。她告诉我她已经把厂子(她后来开了一家玉雕厂)关掉了,店面也关了,现在她在一家企业打工。我听了,不好问厂子和店为什么要关,她要关自然有要关的道理。我问她:“你孩子几年级了?”她回答说:“我没有孩子。为什么非要孩子呢?两个人这样生活着,不是很好吗?”
“那,以后呢?若干年后,”我启发她。
她笑一下,把我的茶杯端起来献给我,说:“小孩是可爱,可是只能可爱一会儿,就烦了!我姐的孩子每回来,每回给我的感觉都一样,我怕了!”
怕,不行。怕是误区。你是让你姐的孩子把你的孩子耽误了。于是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比天比地说了一大通,劝她赶紧的要一个!还来得及,今年你三十五岁,等你到了五十五你的儿子已经长成大小伙了,你就有了定心丸顶梁柱了……
她问我:“您知道我今年多大?”
这回,我看她脖颈,那里平展展的看不出褶皱来,但我还是尽量往大里说:“四十!”
她有点对不住我似的,说:“明年,我五十。”
我相信她。她怎么一下子就五十了呢?人生有如白驹过隙,快啊!但我不能表现出一点诧异来,更不能说,那样她会不自然。我说:“请喝茶!”我说:“你是个好人!”她说:“算是吧。”我说:“那是一定的。”交谈陷入无味中。
这时她问道:“好人、坏人能看出来吗?”我说:“日有所想,夜有所梦,人的面部有许多记忆细胞,全在那儿记着呢,应该能看出来的!”她说:“如果你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你相不相信他会出卖你?”
“不会。”我很自信。
“好,”她严肃起来,说道:“我对他说,我给你三千元人民币,你把杨牧之的事说出来!他说开玩笑!杨牧之能有什么事?我把钱加到三万,他犹豫了;我说给你三十万!不少了!说不说?他问我:‘你一定要知道吗?我说了他会怎样呢?’我对他说,这不是你该问的事,你说不说?他一下硬起来,喊道:‘死都不会说的!’我知道他在讨价还价,这种小人!我也喊:‘三百万!听见没有三百万!如果你说了,这钱全是你的了!’他说了。义愤填膺,说他不讲,别人也会检举的,他是为了国家,于是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不但如此,而且还要帮我分析:他一个星期要吃三次肉的,你想你想,他哪来这么多钱?如果他不挖墓,那他一定抢劫!你信不信?”
我问枫:“女人也会这样吗?给她三千,脱不脱?三万!三十万!”
她说是的。不答应的很少,我承认有不爱钱的女人。但起码目前文艺界、艺术院校不少女孩子经不住诱惑,每到星期六校门外便聚了一地高档车,车里坐着款儿,等着接她们去……
笑话!鬼话!她干吗给我说这个?我一头雾水啊!
枫走后,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我想一个女人,我是说像观音一样圣洁的女人,她嫁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男人呢?如果有一天您在报纸上看到头条新闻这样报导:据可靠消息称:“观音女士出嫁了!”你吃惊吗?
神与人,天与地;神住在天上,人住在地上。如果神来到人间,是住在庙里吗?人如果升入天空,住在月宫吗?不是说高处不胜寒吗?能住吗?好女人不生养,你要吗?神神要捏你的头,往碎里捏,你反抗吗?娃娃再胡闹,你阻止吗?人定胜天,你信吗?枫说那些女孩儿在傍大款,不会吧——不是富贵不能淫吗?枫说我的朋友只要得了大钱就会出卖我,怎么会呐!——不是贫贱不能移吗?
这个世界怎么啦?
贝叶经可以给我答案吗?那我就会寻找贝叶经。
不是我读破它,就是它埋葬我。
香炉里的檀香早已燃尽,而杯中的茶尚有余温。走到窗前,见楼下桑树的叶子一日比一日绿得浓了,浅灰色的空里悬着明亮的太阳,太阳下巨大的和低矮的房子参差不齐的摆在那儿,对面村口传来小贩懒洋洋的叫卖声,楼下给物业塞过钱的拾荒者喊着:“破烂——的卖!”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