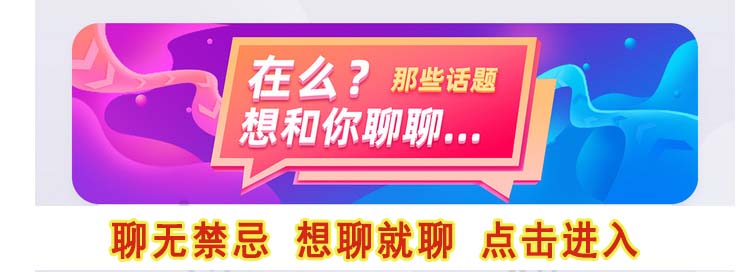新河,发源黑山县,注入绕阳河,河西是小赵家屯,河东是劳改农场四大队。每年七月,一进入连雨天,上游水库泄洪,河水陡涨,水库里的鱼随之放出,下游绕阳河的鱼也会逆流而上。人们互相传告着,“新河来鱼了!”纷纷涌上大坝,用各种工具捕鱼。
爷爷闲暇时,用手工织了一张大网,安上支架和踏杆,在踏杆的前端拴上一根麻绳,就做成扳网。这张扳网,是全村最大的,捕鱼也自然最多。
这天上午,连日的大雨一停,爷爷就带着我,来到新河,选择水边一个离桥不远、水流较缓的位置开始捕鱼。爷爷在网里放些诱饵,将网放到水中。几分钟后,估摸鱼聚得差不多了,就一脚踩住踏杆,双手拽起绳索,把网提起。各种各样的鱼就被提出水面,在网兜里跳跃着,有鲫鱼、黑鱼、窜丁、麦穗,也有泥鳅鱼。我拿着网抄子,把鱼舀出,放入水桶里。
堤坝上,有管教带着一群劳改犯在用麻袋装土,加固大堤。一个三十多岁的“劳改”一边干活,一边盯着我们捕鱼。盯了好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对爷爷说:“您捕的鱼,捕的泥鳅鱼,可不可以送给我一只?”
“你要这鱼有啥用,又没办法做熟了吃。”爷爷不解。
“不用做熟,我想生吃,我好久没吃到鱼了。”
爷爷很好奇,从水桶里捞出一只浑身粘液、蠕动不止的大泥鳅,双手握住,递给他。一名管教也被吸引过来,看他怎样生吃活鱼。
只见“劳改”接过泥鳅鱼,迅速放入口中,一口将头部嚼碎,嘴边流出血丝,鱼尾巴还在唇外摆动着。三下两下,一条大泥鳅就进了肚。
爷爷见他吃得痛快,就把桶里的七八条泥鳅,都捞出来送给他。
“劳改”把泥鳅全部吃完,道声谢谢,才撒欢似地干活去了。
生产队时期,李凤春一直是响当当的执鞭一号大车的车老板。李凤春性格开朗,有风趣,爱逗乐,与人为善,不拘小节,吃苦耐劳,最大的缺点就是喜好杯中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赶车到北地干活,在地头,有几个社员跟他打赌:老李,没酒喝了吧?你要是光着屁股从这里跑到东甸子再回来,我们就每人给你两块钱买酒喝。李凤春问:当真?大家真的每人凑了两块钱,一共十元,用土圪拉压在地上。十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李凤春三下五除二脱衣服,一丝不挂地往东甸子跑。巧的是,东甸子的路上,有个女同志正骑自车经过,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掉头就往回走。开弓没有回头箭,何况能赌到打酒钱,李凤春不管不顾地跑过去,大约二百米的单程距离眨眼时间就跑一来回。嘴里喷着哈气,哆哆嗦嗦地穿上棉衣,揣着钱,熬到中午收工,直奔供销社而去,终于又过了几天酒瘾。
生产队解体时,领导考虑到李凤春赶了二十多年的大车,没让他参与抓阄,就直接把一号大车和驾辕的马分给了他。个别社员有意见,嘀咕几句也就不再言语。而李凤春却似乎没有什么欣喜之情,此后一直郁郁寡欢,偶尔赶车下地干活,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每天三顿酒,村里人都说他泡在酒缸里了。大概生产队的解体对他也是很大的打击,所以更加嗜酒如命。两年后,李凤春患脑溢血去世,时年五十三岁。
王福林,小名王福子,年龄大我一岁,是小赵家有名的孩子头儿,也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表叔。
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春日里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俩趟水过新河,到高山子劳改四大队砖场后身去打鸟。那里沟多树多,鸟自然就多,是春天打鸟的好去处。我俩准备翻过一个大沟,去大地里的台田沟去寻找串鸡、壕溜,这两种鸟比较好打。刚下到沟里,突然从沟底冲出一只野兔,是一只皮毛灰白相间的成年兔子。只见这只野兔窜上沟沿,慌不择路地跑开了。王福林大叫一声“野兔!”率先追了过去,我也随后紧追不舍。追了一会,发现这只兔子没有如平常所见的那样跑得飞快,往往瞬间便无影无踪,而是明显地体力不支,甚至趔趔趄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追下去的信心。翻坡越坎,追了二三百米,野兔离我俩越来越近,它终于跑不动了,跳入一个长满杂草的大坑里,趴着不动了,只有肚子两侧一起一伏,急促地呼吸着,两只长耳朵耷拉着后背上。
王福林先我几步跑到大坑边,却立定在那里,并没有下去捉拿野兔,而是回头对我说,老三,快点,帮我把野兔抓住。我说,你为啥不抓?他说,我怕他咬我,你敢抓吗?我想,兔子有啥可怕的,毫不犹豫地跳入大坑里,紧紧薅住兔子的两只长耳朵,把兔子带出大坑。王福林这时才从我手里接过兔子,狠命往地上一摔,将兔子摔死了。我俩方才细细观瞧,发现这只野兔的后腿受伤了,肌肉外翻,伤得不轻。不然,以人的两条腿,哪能跑得过兔子的四条腿,况且兔子是天生的飞毛腿。
我俩有此收获,也无心再去打鸟,兴匆匆地回家了,兔子被王福林带回他家。到家后,我和姥姥说起此事,姥姥说,你俩追的兔子,咋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不以为然。过了两天,姥姥对我说,走,我带你找老王家去,凭啥他王福子把这么大的兔子独占了,哪管分给你一个兔子大腿也好啊。我说,姥啊,算了,毕竟他比我跑得快,是他先把兔子追到的。姥姥说,那还不是你抓到的。我说,不找了,找也要不回来,兔子早被他家吃光了。姥姥又抱怨几声,这事就这样结束了。
王国忱,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赵家屯生产队长。因脑袋扁平,貌似没有后胸勺,所以人送外号王老扁。值赵家小学夏季农忙假,我和吴大春、赵志双等同学在王老扁的带领下,到北壕铲地。铲地,即古人所谓锄禾。我们几名小学生年纪尚小,对锄禾还不得要领。老扁就手把手地教我们,然后他又做个示范。只听得老扁口中念念有词:“左边搂一下,右边搂一下,苗中间再这么铲一下……”话音未落,只听老扁“哎呀”一声,原来是他一锄头跑偏,把一棵独苗大苞米拦根斩断。
老扁一脸羞赧,尴尬之至。
尤小凤,因天生双眼细小,视物不清,人称尤小眼。一年春节前,屯北李凤春家杀猪请客,邀东邻吴庆富当屠夫并兼作饭的大师傅。尤小眼主动去捞忙,以便混顿吃喝。吴庆富正在厨房忙活,见小眼进来,就伸出右手食指,在小眼眼前晃动,戏弄他说:“给你一根猪尾巴,吃不吃?”尤小眼信以为真,上去就是一口,正咬在吴庆富的手指头上,顿时鲜血淋漓。吴庆富疼得杀猪也似,嚎叫不止。
吴大春,吴庆富长子,长得又瘦又小又黑,是我儿时关系最好的同学和玩伴。
春天里的一天,我俩挎着菜筐,趟过新河,去劳改农场四大队的大地里挖野菜。那时候,四大队播种实行种子拌农药,治了病虫害,却坑了从南方飞来落地觅食的鸟。鸟吃了散落在表土上的玉米种子,重者药死,轻者药晕,因此就常常有人拣到中了毒的鸟。当我俩正要越过一个台田沟时,突然发现沟里有一个大鸟,扑楞着翅膀,想飞,却飞不起来,只贴着沟底往前串。一定是吃了药的鸟!我一阵惊喜。大春眼疾脚快,口里喊着:“是串鸡!”抢在我前面,一个箭步跃进沟里,撵了几步,往前一扑,将大鸟扑在怀里。我站在沟边,正在懊恼被他得了先手,只听大春“妈呀”一声尖叫,身子像是安了弹簧,跳将起来,慌慌忙忙从沟里爬出。
我定晴一看,在沟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冷森森地看着我们,原来是一只猫头鹰。
落后就要挨打。国与国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如此,犯人与犯人之间,更是如此。
老家和高山子劳改农场仅隔一条庞家河,我们称为新河。河西,是我家所在的小赵家屯,河东,就是劳改农场四大队辖区。儿时,一次同小伙伴吴大春、赵志双去四大队挖野菜。趟过新河,翻上东侧大坝,正巧看到一个小队的劳改犯在劳动。两个人一组,抬一个槐条编的大抬筐,一共有六、七组的犯人,从大沟里取土,抬到一个大坑里,用来积肥造粪。一个管教背着一杆破长枪,坐在高处监视,同时手里拿着一段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
赵志双说:“咱坐着歇歇,看老犯干活。”我们就坐在大坝上,看着老犯们一对一对地抬土。
一筐土很沉,他们抬着很吃力。但似乎在搞竟赛,都在拼命抢活,甚至带着小跑,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个个大汗淋漓。
看了二十多分钟,管教一声令下,竟赛停止了。管教指着一组犯人,说:“你俩29筐,老末。”原来他刚才在用树枝划地计数。
这两个可怜的犯人,不用等管教再做吩咐,知道倒数第一要受什么样的惩罚。其中的一个就弯下腰来,撅着屁股,手拄着地,另一个手拿铁锹,高高扬起,“啪”地一声,将锹板打在撅着的犯人屁股上。打一下后,抬着看看管教,管教说:“用力。”于是,又再运力,打的声音也沉闷了一些,“啪、啪、啪……”连打了十铁锹。然后先打人的,把铁锹递给刚刚挨打的,自己也以同样的姿势撅着,受另一个人的打。
打的时间,也是犯人们休息的时间。其他犯人,都坐在地上看,时不时地发出哄笑的声音。打完屁股,犯人们仍旧两人一组,抬着大筐,继续完成前边的劳动。不知道下一回合,哪组落后,谁会挨打,但愿别再是刚才那对犯人,我想。
看完打人,我们赶去挖菜。大春颇有感触地说:“当啥别当犯人,犯啥别犯法。”我和赵志双当然表示同意。吴大春是童年小伙伴中最厚道的人,现在仍然是。
大鵏,一种大型鸟类,比鹅还要大很多。据老人们讲,大鵏,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我的家乡,曾经很常见。每年的春秋两季,大鵏进行南北迁徙时,就会在家乡广袤的田野里停留。
刘福荣一扁担打到一只大鵏,是我从小就听说过的故事。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秋后,刘福荣带着扁担绳索,去大地里拾柴。那时家乡刚刚架设电线,过了牛犄角地,前边的大片田地里,正有两根电线凌空穿跃。走到距电线底下不远,刘福荣就看到一只大鸟点地而飞,有些踉踉跄跄的样子。“是大鵏!”刘福荣不容多想,提着扁担就追了上去。紧赶了几十米,追上那鸟,一扁担拍下去,将大鵏打死。一只大鵏,重达十来斤,刘福荣也顾不上拾柴了,扛着扁担,身后挑着大鵏,喜洋洋地回家了。
此后,人们会经常在电线底下拣到或者捕到各种鸟类,比如大雁、野鸡。原来,这都是电线惹的祸。
对在田野里横空出世的两根细细的电线,在鸟类辽阔的视野里,是很容易忽略的。它们依旧像往常那样迁徙和捕食,一但撞上电线,轻者受伤,重者致死。所以,那只可怜的大鵏,才会被刘福荣一扁担打死。
两年后,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大概鸟类也学会与时俱进,也知道规避风险了。古人守株待兔不成,现代人,守着电线等鸟来撞,也不成了。
我这里要写的小鸟,是我们身边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麻雀,又称家雀儿,是和人类最为亲近的一种野生鸟类。这种鸟可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可是,人类曾经非常对不起它们。从前,就因为争吃了人类的一点点粮食,就被定性为四害之一,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必欲让其绝种而后快。但麻雀并没有远离村落,远离人群,回归大自然,而是仍然和人类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居然在和人类的周旋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终于熬到了好日子,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并被评选为三级保护动物。真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到了五月中下旬,一对对的麻雀就开始互相追逐嬉戏,唧唧喳喳地吵闹不休,说明已到了产蛋孵化的季节。麻雀孵蛋,有两个地方,一是各家各户的屋檐下,二是瓦房屋顶的瓦缝中。瓦缝参差,防雨防风,位置又高,安全系数大,自然就成了麻雀培育下一代的首选之地,也成了孩子们掏鸟蛋的首选去处。
上房揭瓦掏鸟蛋,是被大人们所严厉制止的。制止的原因不是保护它们,而是由于上房揭瓦会踩坏或揭坏瓦片,还有就是不安全,一旦失足滑落下来,非死即伤。俗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小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即使冒着挨打的风险,也没少干上房揭瓦掏麻雀蛋的事。
在生产队队部的瓦房上,我掏了一个麻雀窝,一共三个鸟蛋。当时觉得比别的鸟蛋轻一些,怀疑快要孵出来了吧,所以就没有放在火里烧了吃,而是弄了点棉花裹上,放在炕头,用一只小瓢扣住。三天后,居然成功地孵出一只小麻雀来。光光的身子没有一点绒毛,黄黄的嘴丫儿张得好大。我有点可怜和喜欢它了,决定把它养活。我每天早晨起来和午饭回家、晚上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玉米秸里找虫子喂小鸟。眼看着小麻雀一天天长大,两个月后,终于会飞了,长为成年麻雀了。小家伙特可爱,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它从不乱飞,甚至从没有飞出过屋子,窗户开着也不出去,只是落在窗棂上。屋里的蚊子、苍蝇等小虫子,被它捕个精光。每当我放学回家,就会看见它在窗台上欢快地叫着,我伸出一只手,它就“扑”地一声飞过来,落在我的掌心里。有时我用手指在炕沿上一点,它就会蹦蹦跳跳在走近前来。这时,我就会赏给它一只小虫子吃。后来,这只小麻雀竟然因一点小事而死于非命,让我好一阵伤心。那一天,我和二哥在炕上打扑克,小鸟在一旁蹦蹦跳跳地玩耍。因为出一张牌,我和二哥争吵起来,互不相让。二哥气急败坏,抓起可怜的小鸟,狠狠地往炕上摔去,小鸟当时断了气。我大哭不止,哭声惊动了父亲,父亲很生气,后果也比较严重,当场给了二哥一巴掌。父亲责备二哥说:“打架拿鸟出什么气!多好的小家雀儿,可惜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那种老式的屋檐、老式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麻雀的生存空间也大为狭窄。从前,人之无情,雀何以堪;如今,人之有意,雀谁与归?
土豆花开的时候,麻雀就开始孵蛋了。从麻雀叽叽喳喳地絮窝开始,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对上房揭瓦掏鸟蛋就已经觊觎好久了。那时我们小赵家只有生产队有瓦房,但是房顶一但上人,半个村子都能看到,大人们是不会允许孩子们上房揭瓦的。曾经有一次我们才登墙头上房,就被队长田宝国发现,从房下扔土块让我们下来,鸟蛋没掏到,还挨了顿骂。
一个礼拜天,赵三、吴大春我们三个一合计,柳家中学都是瓦房,麻雀做窝多,又僻静,正是掏鸟蛋的好去处。中学房屋没墙头可上,赵三就从他家把梯子偷出来,我们三个抬着梯子兴匆匆地来到中学院里。我们选准第二趟房中间的瓦房,把梯子架到北墙,正要往上爬,校长董万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上房!我们三个立即撒丫子跑开了。董万德追了几步追不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越过矮墙,逃离校园。
我们正在庆幸侥幸脱险,如果当时已经爬到房上,就肯定被抓了,赵三忽然一拍大腿,不好,我家的梯子丢在那了。我和大春说,别要了,回去肯定挨抓。赵三不干,说他爸知道梯子弄丢了,会打他半死。让赵三自己去找董校长要梯子,他又不肯。我和大春只好硬着头皮陪着赵三回到校园。我们一看,梯子已经斜立在校长办公室窗前。董万德从办公室里看到我们三个探头探脑地,就出来把我们三个揪到办公室,对我们一顿训斥,又让写保证书,站了好久,这才放我们回家,梯子也还给我们了。抬着梯子回家路上,我们三个议论说,再过两年就升中学了,老董头会不会报复。又说,不会的,看他那么大年纪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结果是,过了两年,我们都从赵家小学升入中学,董校长根本没提这事,也许没当回事,也许早就忘记了。一直到初中毕业,董万德也没退休,还是继续当校长,后来又调到沟帮子三高当高中校长,很多年之后才退休回乡养老。儿时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柳家中学,位于小赵家屯和大赵家屯中间,距我家只有大约三百米的路程。而我童年就读的赵家小学,反倒离家稍远一些,在大赵家屯中间的位置。柳家中学有一个阔大的操场,四周绿树成荫,体育设施也较多。因此,童年时,每逢假日,小伙伴们就经常去离家既近又好玩的柳家中学去打闹嬉戏。
一天午后,我和孩子头王福林、赵三赵志双、大眼珠子李国库等童年玩伴在柳家中学操场玩逮人游戏。中间休息时,我双臂吊在篮球架的横梁上打悠荡,身体正晃荡呢,王福林猛然在我后背上推了一把,我登时双手脱离横梁,身体悬空,然后重重摔在地上。落下时,左胳膊肘先着地,当时也没觉得疼痛,只是有些麻木,但起来时左臂却不能活动了。他们几个也无心再做游戏,一起送我回家。送我到当街,就都做鸟兽散了。姥姥正在我家里,向我问明情况,动动我的胳膊,这时,我才感到左胳膊钻心似在疼痛。姥姥说,肯定是错骨缝了。于是对王福林大为埋怨一番,什么不懂事了,欺负比他小的,惹事了又不敢来家道歉,并叮嘱我下次别和他玩。姥姥说,错骨缝不能隔夜,隔夜就端不上了。于是,草草地吃了几口晚饭,就带我去尚驿站找人端骨缝。
尚驿站,是夏家屯的一个自然屯,距我家二里多地,隔着一条县道。尚驿站在县道南,小赵家在县道北。那里有一个老老太会正骨,姥姥认识她。姥姥带着我进入一座茅草房,炕头坐着一个慈祥的老奶奶,笑咪咪地问明情况,然后她挪到炕沿上,让我站在她面前。老奶奶把住我的左胳膊,说,孩子,让奶奶看看,别怕,伤得不重,一会就好。话音未落,我隐约听得咯巴一声,错位的关节就被端上了。胳膊马上就能活动了,也不疼了。姥姥看到外孙子的伤被治好了,很是高兴,问,多少钱?老奶奶说,前后屯住着,要啥钱,领孩子回去吧。
第二天,姥姥把自己家和我家的鸡蛋合在一起,凑了一小筐,用草末蓄上,给那位老奶奶送去了。回来时,姥姥说,这是规矩,人家不要钱但不能不答谢,这鸡蛋本应该让王福林他妈给拿,要不是两家有亲戚,我非找他家要去不可!
王福林是我老舅爷的二儿子,论辈份我得叫二叔。
出小赵家屯往东南五百米,就到了新河的南大桥。南大桥以东,复有一漫水桥,过漫水桥,在左侧的草甸子中,有一座被荒草埋没的土坟。坟前立一块破旧的木牌,上面用红色铅油写着五个大字——王洪达之墓。
从我童年记事时起,到离开家乡来外地工作为止,记忆中,这个写着红字的小木牌,就始终插在那座几乎看不见拱土,也从没有人来祭奠过的荒墓旁。
之所以对王洪达三字这么熟记于心,是因为在当时,王洪达之墓成了我们儿时玩伴们心目中的一个地名,一个座标。劳改四大队,田多,树多,水多,沟沟坎坎多,儿时的活动,大多集中在那片土上。每当去那里打鸟、捉鱼、挖菜、拾荒、拣柴,一过南大桥,就会看见和路过那座并不起眼的荒坟。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是不允许为故去的人树碑立传的。而王洪达死后,居然有一木牌权当墓碑。王洪达何许人也?
据知道一些内情的长辈讲,王洪达原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因为散布反动言论被判劳动教养,并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在高山子教养院(现在的高山子监狱)服刑期满后,就地安置,安排在砖场就业。砖场位于前边说的漫水桥东北二百多米的地方。
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劳教释放犯的称呼是“就业工人”,就业工人比照其他工人,是倍受歧视的。对王洪达在砖厂的工作表现,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件事,却使他一时成为了使人敬佩却不被宣扬的英雄。
那一天,王洪达正在砖厂工作,有一些教养犯在管教的监视下,在机器前脱毛坯。忽然听到有人喊:“犯人逃跑了,快抓呀!”王洪达一抬头,看见有一个犯人跑过来。王洪达身边不远处,就是一大片高高的玉米地,犯人只要一进玉米地,就很难抓捕了。王洪达不容多想,上前拦住犯人。犯人威胁说:“让开,再不让开我动手了。”王洪达的回答是没有让开。犯人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恶狠狠地向王洪达的脑袋砸去。王洪达死命抓住犯人不放,直到犯人被赶上来的管教抓住。而王洪达却倒在了血泊中。
从此,在县道边,在漫水桥一侧的荒草甸子里,就有了一座孤坟和一块鲜红的木碑。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家乡,车辆驶在宽阔的大路上,路过南大桥,漫水桥已不复存在,曾经是桥的位置,已经铺成了厚实的路基。当年那片荒草甸子,都已开发成为了田地,种上了玉米。而王洪达之墓,从此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