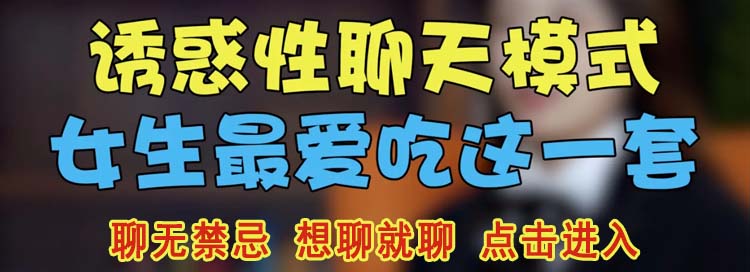三个名人和一块诗刻的故事
贺伟
近代名人汪精卫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在青史上留下芳名,又因投靠日本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33年,汪精卫在庐山对一块古人留下的诗刻产生极大兴趣,特建亭加以保护,留下一段轶闻。
1959年夏季,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庐山开会期间,也在汪精卫感兴趣的诗刻前伫立良久,题联抒怀,给后人留下一段深思。
引起汪精卫、田家英注目的这块诗刻,是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刻于庐山天池峰山道旁的一块巨石上。
王阳明不仅是大哲学家,在文学、书法上亦造诣颇深,又很有军事指挥才能。明朝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阳明指挥大军平息明王朝宗室、宁王朱辰濠在南昌发动的军事叛乱,却差点因此而蒙冤掉了脑袋。他将满腔幽愤倾注于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他却没有料到,他的诗刻竟会引起几百年后的汪精卫、田家英的注意,他在庐山刻诗的故事又会引出后来的故事。
一 王阳明庐山刻诗的故事
前来庐山的宾客在游览完著名景点“仙人洞”后,大都要去参观相隔不远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大天池和龙首崖。
沿着天池峰的山道向前行进,游人们往往会在道旁的一座石亭前停下脚步。原来亭中有块巨石,巨石上端刻着“照江崖”三个楷书大字。字写得极有水平,但无边款。据明朝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桑乔所撰《庐山纪事》中记载,此三个大字为刘世扬所题。刘世扬在嘉靖年间曾在朝廷任给事中,后长期主事庐山白鹿洞书院。“照江崖”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站在这块巨大的崖石上,可以在流过山麓的长江中照照身影;一说是这块巨石十分坚硬、光滑,又呈斜面,象一块镶嵌在山顶的铜镜,可以照出山麓的长江。两种说法都比较夸张,后一种似乎更合理、更美一些。但细心的游者可能会发问,巨石的斜面本是朝里,背对长江,如何能映照长江?这当然只能从广义的空间上来想像,说得过实就缺乏诗意了。
但是,引得游人止步的并不仅仅是“照江崖”三个大字,更重要的是三个字的下方,还刻有一首保护得极好的诗:
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游人们读后,大都会点头赞扬。此诗写得通俗易懂,内容却极为丰富,廖廖数笔,写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你看:山上、山下,直径相隔不远,只是高低不同,却一个是月明星稀、风平林静,任人好生酣睡;一个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将屋顶压得严严实实的茅草卷得漫空乱舞。山上山下,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怎不让人抚掌称奇!
这首诗是谁刻在这儿的?看看边款:“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所作所书,难怪诗好字也好,一手漂亮的行楷,既端庄沉稳,又飘逸秀丽。再看看覆盖巨石的亭子,全由精致的石料搭配、镶嵌而成,6个飞角翘向空中,十分精美别致,远比庐山花径景区中覆盖“花径”两字石刻的木亭高档。石亭无扁额及标识,不知何人所建,建于何时?
建亭的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近代名人汪精卫。他为何要在此建亭?我们稍后再说,还是先来讲讲王阳明刻诗的故事。
王阳明的这首诗表面看来,只是描绘了一种奇妙的大自然现象,其实,诗的背后,隐藏着王阳明深深的幽愤和不平。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祖藉浙江余姚,因曾隐居绍兴的“阳明”洞,自称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他虽然官至兵部尚书,职位很高,但却是以哲学成就而载入史册。
王阳明是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统兵打仗也不外行。他在天池峰山道旁留下的这首诗刻,就和他的一次军事行动及由此而产生的幽愤有直接关系。
为了弄清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庐山秀峰寺现存的王阳明撰写的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叫《正德庚辰平宸濠题识》,写的是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赣南的王阳明接受皇帝朱武宗(厚照)的圣命,指挥江西一带的讨逆大军,与朱宸濠大战于鄱阳湖,击败叛军,生俘朱宸濠。因此,这块石碑又被称为“纪功碑”。
然而,细读碑文,却颇有些令人感到困惑。
碑文前面明确写道:“正德巳卯六月乙亥,宁潘宸濠以南昌叛。……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但接下来却是:“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碑文前面写得清请楚楚,是王阳明率兵克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叛军都被扫平。但接下来又说,天子闻变亲率大军前来平叛,俘获了朱宸濠。那么,究竟是谁平定了叛乱,擒获了宁王?并非王阳明行文不清,而是这其中大有隐情,王阳明有意要这样写的。
原来武宗的宦官、宠臣张永、江彬、许泰等人对王阳明嫉恨已久,他们接到王阳明平定叛乱的捷报后,对武宗说宁王叛乱前曾与王阳明联系过,王阳明却胆敢密而不报,极有可能亦存反心,看哪边得势就往那边靠,因此对王阳明需加提防。武宗一听,十分恼怒,明知叛乱已平、朱宸濠被擒,还是亲率大军前来“平叛”。此行如发现王阳明果有异常举动,可随时处置,以免再留下隐患。
王阳明探知内情,惊恐不安,只好将自己的“战利品”朱宸濠交给武宗大军的先行官张永,把“首功”让给他,希望他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同时,王阳明向皇上重新报捷,将平叛擒王的“功劳”归于“天子”,并一再表明对皇上的忠诚。武宗命王阳明在九江一带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后再做处理。王阳明虽然暂时避免了劫难,但到底是心有不甘,所以在写“纪功碑”时,还是委婉地透露自己本应得的功劳。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愤愤不平又忧虑不安的心境中上的庐山。
四月的庐山,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坡草新绿,山花始开,错落高低的峰峦在飘渺的云雾中时隐时现、迷蒙绰约。如诗如画的美景并未撩起王阳明的诗兴,倒是他夜宿天池峰寺庙时遇见的一种自然现象触动了他的思绪:山上月明星稀、风平林静,山下却是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同顶一面天,同处一块地,只因高低位置不同,区别竟是如此之大,身处两地之人又如何能明晓彼此的处境、心态。王阳明由此而联想到,自己本是对皇上一片忠诚,拼着身家性命浴血彊场;而皇帝高高在上,哪能明察自己的处境和真情!又不派人下来调查,反而听信周围那帮小人的谗言。自己不但无功,反而要获罪,焉能不令人愤愤难平!
正是这种感慨,促动王阳明写下了这首明是描绘自然现象、实是暗寓心中幽愤的诗作。他的幽愤在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中表露得明显一些:“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王阳明在诗中忍不住要咒骂那些“木魅山妖”不安好心,偷盗云水酿成风雨,搅得人间不得安宁。当然,这首诗他是不敢公然刻在岩石上。
王阳明蕴藏在这些诗文中的幽愤还比较含蓄,但他无意中写的一首有关“佛灯”的诗,却差点给他惹了祸。“佛灯”被当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列为庐山“三大自然奇谜”之一,说的是在天池峰一带,月明星稀之夜,偶尔会看见山腰出现几十、甚至上百团荧荧火光,不停地游动,时大时小,时聚时散,被称为“神灯”,亦称“佛灯”。“佛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磷火,有的说是山中埋有矿藏、矿藏发出的光,有的说是星星映在半山云团上的反光,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答案。“佛灯”十分难见,偏偏就让王阳明碰见了,他喜而作诗曰:“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王阳明真是一时大意,本身就在“待命”受审期间,他竟然还敢说“拄杖夜撞青天开”?“青天”是什么?“青天”也可以说就是“皇天”,他居然敢把“青天”撞开,他把“天子”放在何处?这不是公然蔑视“天子”么?如果被嫉恨他的那些宦官、宠臣注意,说有诗为证,昭然若揭,他果有反心,他还能说得清楚么?
万幸,此诗并未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对朝廷忠心耿耿的王阳明最终还是洗清了冤屈,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他的这段往事,这份幽愤,永远保存在了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
二 汪精卫缘何建石亭保护王阳明诗刻
几百年过去了,人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王阳明留在庐山的诗刻、碑文仍然完好如故。
1933年夏初的一天,天池峰山道旁刻有王阳明诗作的“照江崖”巨石前,久久地伫立着一个中年男子,他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对王阳明极有研究的汪精卫仔细咀嚼着这首诗,再结合王阳明滞留庐山的经历,慢慢品出了藐似描绘大自然奇观的背后所蕴含的幽愤,引起了汪精卫强烈的共鸣。近些年来,他的内心深处也积压了太多的幽愤。
汪精卫虽然只比蒋介石大4岁,但资历却比蒋要深得多,影响也曾比蒋要大得多,威信也曾比蒋要高得多。1905年,22岁的汪精卫在日本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当选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而此时,18岁的蒋介石还是宁波箭金学堂的学生。1910年,27岁的汪精卫在京城刺杀摄政王载沣,失手被捕,举国震动,他在狱中写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民间争相传诵,人人仰慕英雄;而此时,23岁的蒋介石,只是日本“振武学校”的一名学生。1925年7月1日,汪精卫被推举为广东革命政府主席,紧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又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南方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而此时,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8名委员中的一员,党、政方面没有任何职务。然而,没几年,颇有心计的蒋介石七搞八搞,就把党、政、军大权都揽到了手。汪精卫再不服气,再憋屈,也只能屈居蒋之后。
虽然汪精卫表面看起来仍是那么风度翩翩,谈笑自若,但他内心深处时常的“风雨大作”,又岂是旁人所能知晓。正如王阳明诗中所描绘的自然奇观一样,“山上”、“山下”,因所处地位不同,境遇也完全不同,“山上”、“山下”的人都难以知晓彼此的境遇。人世间不也是如此吗?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有过的经历不同,彼此之间的心境也有着巨大的差别,互相之间都难以知晓、理解。
汪精卫十分喜欢王阳明的这首诗,他看到刻诗的“照江崖”巨石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天长日久,难免会逐渐磨损、洇没。他想到前两年,文人雅士陈三立、李凤高、吴宗慈等人筹资,在花径景区建亭,保护刻有相传是白居易手迹的“花径”二字的石块,一时传为佳话。于是,汪精卫也决定自己出资建亭保护王阳明诗刻,并且亭子一定要比陈三立等人建的木亭要好,要更高档。
不久,一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分精巧别致的六角石亭便耸立在“照江崖”巨石之上,将整块巨石完全笼罩于亭中,不但起到了保护诗刻的作用,更为诗刻增添了光彩,使诗刻、巨石、石亭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汪精卫对石亭很满意,想到自己很可能因建石亭将会和历史上的大名人王阳明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自是很开心。他特赋诗一首《阳明诗石亭落成题壁》:“瀑响龙潭静可听,兼收画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双镜,吴楚青苍共一屏。世态佛灯搀鬼火,道心明月定风霆。飘然拄杖撞天去,片石空留手泽馨。”汪诗描写了石亭附近飞瀑龙潭的胜景和远眺长江湖泊、苍茫大地的远景,但重点还是要抒发内心的情感。诗中表露自己要象王阳明一样,面对“鬼火”,仍是心如明月般澄静从容,平定风波。他甚至想象自己也能象王阳明一样“飘然拄杖撞天去”,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也可聊以发泄一下内心深处的幽愤。
但汪精卫到底与王阳明不同。王阳明的确并无反心,后来还升了大官,而汪精卫为了重温“老大”的旧梦,不惜叛国投敌做傀儡,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三 田家英读诗感叹,写联抒怀
1959年7月底的一天下午,庐山天池峰的山道上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们是上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一行人慢慢走着,来到了王阳明诗刻前。
众人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石上的刻诗。田家英说道:“王阳明是大理学家,据说很会‘格物致知’,我不大信服。但这首诗倒好象有些预见性,诗中描写的自然现象和我们现在开会的情形似乎有些相似,‘山下’的人,又怎么知道‘山上’开会的情景呀。”众人听了,都一时无语。
是啊,“山下”的人都以为“山上”开的重要会议,参会的都是德高望重、高瞻远瞩的领导,一定是同心同德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又怎会知晓会议的真实情况。
7月2日开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为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调整修改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指标,参会的领导都心情愉快。田家英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十分了解,极为担忧,因此,对此次庐山会议开始纠“左”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拥护。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史称“万言书”),详细谈了自己对当前“左倾”、“冒进”的错误倾向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真实看法,要求中央深挖原因,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于7月16日给彭德怀的长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大会讨论。田家英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总的意见。谁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大会上,对彭德怀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会议方向骤然转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由轻松愉快的“神仙会”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路线”斗争会。中央还临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大为困惑、大为不解,也极为不满。
心情极为焦虑、沉重的田家英和李锐等人在山道上散散心,王阳明的诗又引发了他的感叹。站在刻有王诗的“照江崖”巨石旁,37岁的田家英眺望着山麓绵延起伏的山岗、奔腾不息的长江,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田家英出身四川的贫苦人家,初中没读完便去药店当学徒,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6岁加入共产党,靠刻苦自学成为党内著名的“秀才”,28岁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极爱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深受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他极为敬重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林则徐,特意请篆刻家将林则徐的两句名诗刻为两枚对章:“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林诗“敢”作“岂”)。他也极钦佩舍生取义、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他的书房“小莽苍苍斋”就是沿用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解放后,田家英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而勤奋工作,他经常受毛泽东委托,去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及时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在陪同毛泽东前来庐山开会的途中和会议前期,田家英还多次向毛泽东坦率地谈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庐山会议的突然转向感到万分震惊,对敢说真话的同志遭到严厉打击而极为不满,他更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刻上的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李锐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本是岳阳楼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这幅对联,更熟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这副对联,正好婉转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使他免遭厄运,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象以前那样信任。田家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怪圈,即它所倡导的人格恰恰是现实中最易碰壁和受伤的人格。儒家文化要求君子为人方正,有节操、有原则、不苟且,故有称其为方型人格,其对立面便是所谓“圆滑”,见风使舵,不讲原则和立场,还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方型人格在与现实的屡屡冲撞磨擦中,往往会被逐渐打磨成“圆滑”型人格。能够始终坚持不被外界改造、坚守自己方正人格的人很少,田家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1980年3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为“文革”中惨死的田家英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力群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就对田家英的高贵人品做了充分肯定:“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在庐山天池峰石亭前的泥地上书写对联时,心情是多么沉重啊!虽然写在泥地上的对联已被岁月的风尘抹去,但时间的流水并不能淘去所有的往事。李锐在几十年后写的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此事,并特意为此赋诗一首:“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
王阳明是大哲学家,以善于“格物致知”而称著,但他却未能从“山上”的月明林静而“格”出“山下”的风雨大作,可见大自然中实在充满了太多的奇妙和奥秘。比大自然更加奥秘难测的应是人世间、人的内心世界吧。
王阳明的诗还要在天池峰的山道旁继续留存下去,还会有很多后人在诗刻前伫步,默默的咀嚼,不知又会从中得到什么感悟和启迪。
贺伟
近代名人汪精卫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在青史上留下芳名,又因投靠日本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33年,汪精卫在庐山对一块古人留下的诗刻产生极大兴趣,特建亭加以保护,留下一段轶闻。
1959年夏季,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庐山开会期间,也在汪精卫感兴趣的诗刻前伫立良久,题联抒怀,给后人留下一段深思。
引起汪精卫、田家英注目的这块诗刻,是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刻于庐山天池峰山道旁的一块巨石上。
王阳明不仅是大哲学家,在文学、书法上亦造诣颇深,又很有军事指挥才能。明朝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阳明指挥大军平息明王朝宗室、宁王朱辰濠在南昌发动的军事叛乱,却差点因此而蒙冤掉了脑袋。他将满腔幽愤倾注于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他却没有料到,他的诗刻竟会引起几百年后的汪精卫、田家英的注意,他在庐山刻诗的故事又会引出后来的故事。
一 王阳明庐山刻诗的故事
前来庐山的宾客在游览完著名景点“仙人洞”后,大都要去参观相隔不远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大天池和龙首崖。
沿着天池峰的山道向前行进,游人们往往会在道旁的一座石亭前停下脚步。原来亭中有块巨石,巨石上端刻着“照江崖”三个楷书大字。字写得极有水平,但无边款。据明朝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桑乔所撰《庐山纪事》中记载,此三个大字为刘世扬所题。刘世扬在嘉靖年间曾在朝廷任给事中,后长期主事庐山白鹿洞书院。“照江崖”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站在这块巨大的崖石上,可以在流过山麓的长江中照照身影;一说是这块巨石十分坚硬、光滑,又呈斜面,象一块镶嵌在山顶的铜镜,可以照出山麓的长江。两种说法都比较夸张,后一种似乎更合理、更美一些。但细心的游者可能会发问,巨石的斜面本是朝里,背对长江,如何能映照长江?这当然只能从广义的空间上来想像,说得过实就缺乏诗意了。
但是,引得游人止步的并不仅仅是“照江崖”三个大字,更重要的是三个字的下方,还刻有一首保护得极好的诗:
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游人们读后,大都会点头赞扬。此诗写得通俗易懂,内容却极为丰富,廖廖数笔,写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你看:山上、山下,直径相隔不远,只是高低不同,却一个是月明星稀、风平林静,任人好生酣睡;一个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将屋顶压得严严实实的茅草卷得漫空乱舞。山上山下,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怎不让人抚掌称奇!
这首诗是谁刻在这儿的?看看边款:“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所作所书,难怪诗好字也好,一手漂亮的行楷,既端庄沉稳,又飘逸秀丽。再看看覆盖巨石的亭子,全由精致的石料搭配、镶嵌而成,6个飞角翘向空中,十分精美别致,远比庐山花径景区中覆盖“花径”两字石刻的木亭高档。石亭无扁额及标识,不知何人所建,建于何时?
建亭的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近代名人汪精卫。他为何要在此建亭?我们稍后再说,还是先来讲讲王阳明刻诗的故事。
王阳明的这首诗表面看来,只是描绘了一种奇妙的大自然现象,其实,诗的背后,隐藏着王阳明深深的幽愤和不平。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祖藉浙江余姚,因曾隐居绍兴的“阳明”洞,自称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他虽然官至兵部尚书,职位很高,但却是以哲学成就而载入史册。
王阳明是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统兵打仗也不外行。他在天池峰山道旁留下的这首诗刻,就和他的一次军事行动及由此而产生的幽愤有直接关系。
为了弄清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庐山秀峰寺现存的王阳明撰写的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叫《正德庚辰平宸濠题识》,写的是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赣南的王阳明接受皇帝朱武宗(厚照)的圣命,指挥江西一带的讨逆大军,与朱宸濠大战于鄱阳湖,击败叛军,生俘朱宸濠。因此,这块石碑又被称为“纪功碑”。
然而,细读碑文,却颇有些令人感到困惑。
碑文前面明确写道:“正德巳卯六月乙亥,宁潘宸濠以南昌叛。……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但接下来却是:“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碑文前面写得清请楚楚,是王阳明率兵克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叛军都被扫平。但接下来又说,天子闻变亲率大军前来平叛,俘获了朱宸濠。那么,究竟是谁平定了叛乱,擒获了宁王?并非王阳明行文不清,而是这其中大有隐情,王阳明有意要这样写的。
原来武宗的宦官、宠臣张永、江彬、许泰等人对王阳明嫉恨已久,他们接到王阳明平定叛乱的捷报后,对武宗说宁王叛乱前曾与王阳明联系过,王阳明却胆敢密而不报,极有可能亦存反心,看哪边得势就往那边靠,因此对王阳明需加提防。武宗一听,十分恼怒,明知叛乱已平、朱宸濠被擒,还是亲率大军前来“平叛”。此行如发现王阳明果有异常举动,可随时处置,以免再留下隐患。
王阳明探知内情,惊恐不安,只好将自己的“战利品”朱宸濠交给武宗大军的先行官张永,把“首功”让给他,希望他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同时,王阳明向皇上重新报捷,将平叛擒王的“功劳”归于“天子”,并一再表明对皇上的忠诚。武宗命王阳明在九江一带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后再做处理。王阳明虽然暂时避免了劫难,但到底是心有不甘,所以在写“纪功碑”时,还是委婉地透露自己本应得的功劳。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愤愤不平又忧虑不安的心境中上的庐山。
四月的庐山,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坡草新绿,山花始开,错落高低的峰峦在飘渺的云雾中时隐时现、迷蒙绰约。如诗如画的美景并未撩起王阳明的诗兴,倒是他夜宿天池峰寺庙时遇见的一种自然现象触动了他的思绪:山上月明星稀、风平林静,山下却是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同顶一面天,同处一块地,只因高低位置不同,区别竟是如此之大,身处两地之人又如何能明晓彼此的处境、心态。王阳明由此而联想到,自己本是对皇上一片忠诚,拼着身家性命浴血彊场;而皇帝高高在上,哪能明察自己的处境和真情!又不派人下来调查,反而听信周围那帮小人的谗言。自己不但无功,反而要获罪,焉能不令人愤愤难平!
正是这种感慨,促动王阳明写下了这首明是描绘自然现象、实是暗寓心中幽愤的诗作。他的幽愤在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中表露得明显一些:“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王阳明在诗中忍不住要咒骂那些“木魅山妖”不安好心,偷盗云水酿成风雨,搅得人间不得安宁。当然,这首诗他是不敢公然刻在岩石上。
王阳明蕴藏在这些诗文中的幽愤还比较含蓄,但他无意中写的一首有关“佛灯”的诗,却差点给他惹了祸。“佛灯”被当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列为庐山“三大自然奇谜”之一,说的是在天池峰一带,月明星稀之夜,偶尔会看见山腰出现几十、甚至上百团荧荧火光,不停地游动,时大时小,时聚时散,被称为“神灯”,亦称“佛灯”。“佛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磷火,有的说是山中埋有矿藏、矿藏发出的光,有的说是星星映在半山云团上的反光,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答案。“佛灯”十分难见,偏偏就让王阳明碰见了,他喜而作诗曰:“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王阳明真是一时大意,本身就在“待命”受审期间,他竟然还敢说“拄杖夜撞青天开”?“青天”是什么?“青天”也可以说就是“皇天”,他居然敢把“青天”撞开,他把“天子”放在何处?这不是公然蔑视“天子”么?如果被嫉恨他的那些宦官、宠臣注意,说有诗为证,昭然若揭,他果有反心,他还能说得清楚么?
万幸,此诗并未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对朝廷忠心耿耿的王阳明最终还是洗清了冤屈,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他的这段往事,这份幽愤,永远保存在了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
二 汪精卫缘何建石亭保护王阳明诗刻
几百年过去了,人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王阳明留在庐山的诗刻、碑文仍然完好如故。
1933年夏初的一天,天池峰山道旁刻有王阳明诗作的“照江崖”巨石前,久久地伫立着一个中年男子,他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对王阳明极有研究的汪精卫仔细咀嚼着这首诗,再结合王阳明滞留庐山的经历,慢慢品出了藐似描绘大自然奇观的背后所蕴含的幽愤,引起了汪精卫强烈的共鸣。近些年来,他的内心深处也积压了太多的幽愤。
汪精卫虽然只比蒋介石大4岁,但资历却比蒋要深得多,影响也曾比蒋要大得多,威信也曾比蒋要高得多。1905年,22岁的汪精卫在日本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当选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而此时,18岁的蒋介石还是宁波箭金学堂的学生。1910年,27岁的汪精卫在京城刺杀摄政王载沣,失手被捕,举国震动,他在狱中写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民间争相传诵,人人仰慕英雄;而此时,23岁的蒋介石,只是日本“振武学校”的一名学生。1925年7月1日,汪精卫被推举为广东革命政府主席,紧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又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南方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而此时,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8名委员中的一员,党、政方面没有任何职务。然而,没几年,颇有心计的蒋介石七搞八搞,就把党、政、军大权都揽到了手。汪精卫再不服气,再憋屈,也只能屈居蒋之后。
虽然汪精卫表面看起来仍是那么风度翩翩,谈笑自若,但他内心深处时常的“风雨大作”,又岂是旁人所能知晓。正如王阳明诗中所描绘的自然奇观一样,“山上”、“山下”,因所处地位不同,境遇也完全不同,“山上”、“山下”的人都难以知晓彼此的境遇。人世间不也是如此吗?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有过的经历不同,彼此之间的心境也有着巨大的差别,互相之间都难以知晓、理解。
汪精卫十分喜欢王阳明的这首诗,他看到刻诗的“照江崖”巨石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天长日久,难免会逐渐磨损、洇没。他想到前两年,文人雅士陈三立、李凤高、吴宗慈等人筹资,在花径景区建亭,保护刻有相传是白居易手迹的“花径”二字的石块,一时传为佳话。于是,汪精卫也决定自己出资建亭保护王阳明诗刻,并且亭子一定要比陈三立等人建的木亭要好,要更高档。
不久,一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分精巧别致的六角石亭便耸立在“照江崖”巨石之上,将整块巨石完全笼罩于亭中,不但起到了保护诗刻的作用,更为诗刻增添了光彩,使诗刻、巨石、石亭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汪精卫对石亭很满意,想到自己很可能因建石亭将会和历史上的大名人王阳明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自是很开心。他特赋诗一首《阳明诗石亭落成题壁》:“瀑响龙潭静可听,兼收画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双镜,吴楚青苍共一屏。世态佛灯搀鬼火,道心明月定风霆。飘然拄杖撞天去,片石空留手泽馨。”汪诗描写了石亭附近飞瀑龙潭的胜景和远眺长江湖泊、苍茫大地的远景,但重点还是要抒发内心的情感。诗中表露自己要象王阳明一样,面对“鬼火”,仍是心如明月般澄静从容,平定风波。他甚至想象自己也能象王阳明一样“飘然拄杖撞天去”,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也可聊以发泄一下内心深处的幽愤。
但汪精卫到底与王阳明不同。王阳明的确并无反心,后来还升了大官,而汪精卫为了重温“老大”的旧梦,不惜叛国投敌做傀儡,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三 田家英读诗感叹,写联抒怀
1959年7月底的一天下午,庐山天池峰的山道上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们是上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一行人慢慢走着,来到了王阳明诗刻前。
众人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石上的刻诗。田家英说道:“王阳明是大理学家,据说很会‘格物致知’,我不大信服。但这首诗倒好象有些预见性,诗中描写的自然现象和我们现在开会的情形似乎有些相似,‘山下’的人,又怎么知道‘山上’开会的情景呀。”众人听了,都一时无语。
是啊,“山下”的人都以为“山上”开的重要会议,参会的都是德高望重、高瞻远瞩的领导,一定是同心同德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又怎会知晓会议的真实情况。
7月2日开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为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调整修改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指标,参会的领导都心情愉快。田家英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十分了解,极为担忧,因此,对此次庐山会议开始纠“左”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拥护。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史称“万言书”),详细谈了自己对当前“左倾”、“冒进”的错误倾向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真实看法,要求中央深挖原因,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于7月16日给彭德怀的长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大会讨论。田家英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总的意见。谁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大会上,对彭德怀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会议方向骤然转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由轻松愉快的“神仙会”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路线”斗争会。中央还临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大为困惑、大为不解,也极为不满。
心情极为焦虑、沉重的田家英和李锐等人在山道上散散心,王阳明的诗又引发了他的感叹。站在刻有王诗的“照江崖”巨石旁,37岁的田家英眺望着山麓绵延起伏的山岗、奔腾不息的长江,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田家英出身四川的贫苦人家,初中没读完便去药店当学徒,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6岁加入共产党,靠刻苦自学成为党内著名的“秀才”,28岁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极爱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深受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他极为敬重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林则徐,特意请篆刻家将林则徐的两句名诗刻为两枚对章:“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林诗“敢”作“岂”)。他也极钦佩舍生取义、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他的书房“小莽苍苍斋”就是沿用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解放后,田家英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而勤奋工作,他经常受毛泽东委托,去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及时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在陪同毛泽东前来庐山开会的途中和会议前期,田家英还多次向毛泽东坦率地谈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庐山会议的突然转向感到万分震惊,对敢说真话的同志遭到严厉打击而极为不满,他更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刻上的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李锐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本是岳阳楼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这幅对联,更熟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这副对联,正好婉转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使他免遭厄运,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象以前那样信任。田家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怪圈,即它所倡导的人格恰恰是现实中最易碰壁和受伤的人格。儒家文化要求君子为人方正,有节操、有原则、不苟且,故有称其为方型人格,其对立面便是所谓“圆滑”,见风使舵,不讲原则和立场,还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方型人格在与现实的屡屡冲撞磨擦中,往往会被逐渐打磨成“圆滑”型人格。能够始终坚持不被外界改造、坚守自己方正人格的人很少,田家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1980年3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为“文革”中惨死的田家英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力群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就对田家英的高贵人品做了充分肯定:“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在庐山天池峰石亭前的泥地上书写对联时,心情是多么沉重啊!虽然写在泥地上的对联已被岁月的风尘抹去,但时间的流水并不能淘去所有的往事。李锐在几十年后写的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此事,并特意为此赋诗一首:“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
王阳明是大哲学家,以善于“格物致知”而称著,但他却未能从“山上”的月明林静而“格”出“山下”的风雨大作,可见大自然中实在充满了太多的奇妙和奥秘。比大自然更加奥秘难测的应是人世间、人的内心世界吧。
王阳明的诗还要在天池峰的山道旁继续留存下去,还会有很多后人在诗刻前伫步,默默的咀嚼,不知又会从中得到什么感悟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