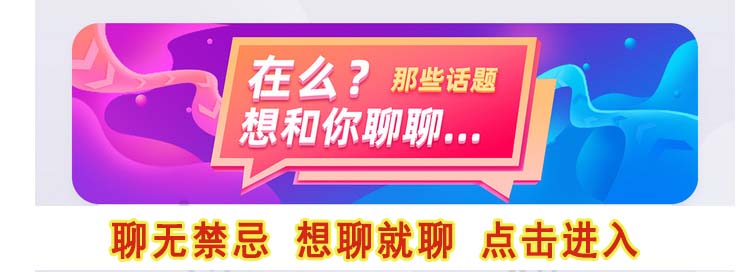他们摸起刻刀和钉子,他们坐在海印桥上
雕刻时光。
湿气笼罩着珠江,低矮的天空
飞过几只温暖的鸽子
命犯桃花的人,三滴五滴,蹲在树上
傍晚时,他们扛着梯子走了
我留在17楼的窗口
将自己扩张成一个剧院或孤岛
而你坐在哪里?
你带我去过朗拿度,星巴克,和避风塘
我只带你去过乌衣巷
刻在墙上的乌衣巷,一些旧时光
此后,我每天去同一个地方
每天见到同一个女人,与我擦肩而过
她的丰满,她的邪恶,她的床
她为我敞开漆黑的身体,和漆黑的光。
2004/12/2/
花园在默默地燃烧。
蓓蕾在绿叶中
就象车灯在黑夜中,
崇尚忍受,不出声响。
花园的鸟兽,幼虫
陶醉在窒息中。
自然的呼啸,飞机的翅膀
什么时候听不到了?
不知不觉移来雨——
湿泥敲在院墙上。
枝摧叶折,墙倒塌。
草木奔向了季节,象人体。
春天作为四个原色习俗中的一个,已经沉入松散的根系
或者飘上蓬蓬的云端。三年之久,我不曾见她串过一次门
村口的村民于是越站越多,寂静的远方空无一物
电线杆一根一根排过来,不抵达你的脸不罢休
春天作为原色习俗中的一个,迷失在串门的路上
村口没有了站更多人的地方,因为其他三个缤纷的习俗
搭配出一朵花,同样挤在人群当中使计划生育依旧有效
电线杆开始收购天空,摇摇雪白的骨骼欲坠
春天作为四个原色习俗的一个,或者沉入根系
或者飘上云端。但这并不意味着
从此你将和青草色春天绝缘∶春天还作为另一种习俗存在
比如,花一块钱坐8路公共汽车,花上十块钱买一张门票
再径直走入。春天就坐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俯首静候
参观之后不妨想一想汽车开来的村口∶人都去了哪里?
《我希望雨下得长久》
我希望雨下得长久,
它果然就下得长久∶
从你的头上一直下到我的头上,
从你的阳春一直下到我的杨村。
有人说∶两个人分担痛苦
要比一个人承受喜悦好,
因为除了喜悦还有痛苦
而除了痛苦都没有什么。
那么两个人分担一场凉雨
将会怎样?
我们会在树下躲雨
身上披着淋湿的树神。
我希望雨下得长久,
它果然就倾斜了诉说的态度,
仿佛我要它下得短暂
它就停在我的头上,制造彩虹。
在那个以青色为主的岛上,
三里屯酒吧
是个比妓院更可疑的地方。
当我和你在门口的霓虹灯下
象兄弟一样
搭着兄弟的胳膊走出来时,
的士司机
在车窗后面微笑。
我用手指扣扣发凉的车门。
司机的微笑
也因为我们选择坐他的车
变得宽容。
如果真象他的微笑暗示的那样,
我和你
是一对相互爱着的男人。
我和你从里面走出来,
同样会开心地过这一晚。
你住的那个院子里的树真的不错
今天我脑袋里已经出现了三次
还有牵牛花,养在盆里的
“直到昨天才长出一棵小小的芽”
你说。
你还在露天楼梯的转角
点着另外的小植物∶
“这,这,这,也是我种的”。
我梦见有人把烟头扔在着名的草船
甲板滋滋滋地燃烧
一直烧到了我的家乡
资江边上
枫树坳里
我家的草垛插满火箭
牛蹄踏破墙橹
奶奶满头白发红光一闪
灰飞烟灭
一群人手忙脚乱
抬着我的床
朝着火海一路小跑
穿越华容山道
喊着给我举行一场火葬
绊倒在铁索桥
我躺在床上
哇哇大叫却动弹不了
火的舌头在我身上舔
舔到我座下的马鞍我的耳背
我醒了
一眼看见床头的中国地图
面目全非
长江两岸湖南湖北
都完蛋了
被子正在冒烟
烟冒得不大于是我把它扑灭了
星期天是一个很象星期一的日子
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很象
为了度过其中的一个
我会到另外一个学校
另外一个男人那里去
他和我抽一个牌子的烟
他扶弄过我的下面
并且一再示意我
和他的一个女人大声地
大声地调情
因此我们是亲密的
我会把烟头扔在渭河平原上
另外一个烟头的附近
这个烟头的主人上午告诉我说
咸阳有一个国际机场
可以去好多好多地方
在电影《钢琴师》中
主演在一间寄居的房间中
躲避德军的杀害
两周没有人送食物来了
当他拿着刀凝视最后一个土豆
这浑身长着绿芽的土豆
母亲很早以前就告诉我
长芽土豆吃了会有毒的土豆
他精心的切成两半
切面上可以看到土豆肉身有一些
暗黑的区域
他必须节约
这一顿他吃下了一半
幸好他只吃了一半
后来他就病倒在床上
在赶来的朋友帮助中侥幸逃过一命
当他好转身体
从窗口偷偷望出去
纳粹警察局正乱成一团
波兰人民已在秘密、小规模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