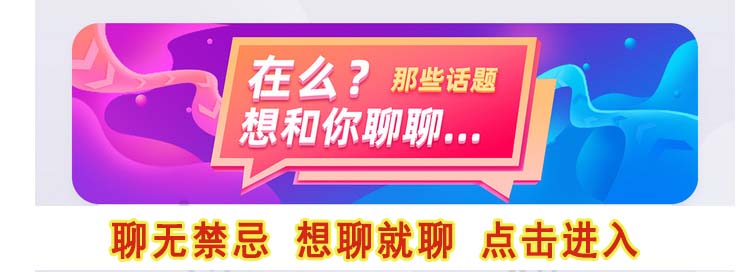多年前在省城漂泊,疲倦的翅膀舞动,浑如故乡天空一闪而过的熟悉的麻雀。在这样的心境下,诗歌《一只鸟从故乡飞过》应运而生。一直念念不忘1993年的那个秋日,在省教育学院图书馆惊见我的诗歌亮相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的欣喜,温暖了之后相当漫长的时日。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回忆,是因为那几行文字的发表及文字本身,实在有太多的内涵。有时甚至想,那是不是多年来我不肯轻弃文学梦想的一个支点呢?
阅读是艺术的再创作。一件作品抑或文字诞生,写作者已然完成了他的劳作,剩下的事情就要靠读者来完成了。文艺学上有共鸣之说,而共鸣的时间跨度,有时拖沓的惊人。美国女子艾米丽?迪金森,一生沉寂,孤苦地与文字相依至终。谁会料想,其身后现世的文字,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风暴,从而成就了她美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美名。斯人已去,文脉悠悠。
读到散文《永远的麻雀》,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早年曾经写过的那首诗歌。而此文带给我的冲击,远非迪金森文字那般令人唏嘘的回应久远。作者东风染碧树,于我而言并非陌生。我们笔墨邂逅于读者杂志官方论坛,文来字去,相互知晓。记得我的文字曾被她细读,而后知道她还经营着一个网上散文沙龙。应邀去过她的园子,到她组织的QQ群参与过有关散文的评议。说心里话,能在喧嚣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固守精神的一方孤岛,这样的举措足以令喜好文字的我肃然起敬。
虽然因我的惫懒和时间关系,近来和东风染碧树接触不多,但她的勤勉和努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作为一个钟爱文字的写作者,偶尔提笔为同道的耕耘摇旗呐喊,看似在对别人的文字评头论足,不过是对孤独写作中的我一种变相的自怜罢了。因此,我的感受,是不好作什么文学评论看的。既然有感于心,发而为文,只能委屈有耐心的读者了。
曾经著文论及散文的题材。什么样的题材适合入笔呢?季羡林老人说小事情易感人。他指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既然“真情”为要,那么题材的限制就不必过多拘泥。我非常赞同从自己最熟悉的人或事写起,在我的论说里也多次提及。小与大的关系是辨证的,以小见大,大中取小,相得益彰。东风染碧树从麻雀落笔,算是一个巧妙的切入。麻雀的知名度,有助于此文的阅读面,但也增加了文字新奇的难度。读罢此文,我感到没有失望。
首先,作者起笔不俗:“如果美专指别致的外形鲜艳的色彩,那麻雀怎么也不可以用漂亮来形容:最常见的略圆的头,除了眼睛附近左右两条白色外,其它地方都是灰褐色,尖尖的深褐色喙平淡无奇,又小又圆的眼睛如墨,闪着星星亮光,但与灰褐色的头并不能形成鲜明的对比;太过纤巧的身子,覆了浓浓淡淡的褐色羽毛,虽说那深与浅的布局异常精致,但因为色彩相近,毕竟整体看起来没有靓色;棕黑色的尾巴齐齐的,打开时也没有扇子的感觉;细小的脚,弱得让人担心禁不住全身的重量……小小的麻雀,太过普通,与鸟类中的美女帅哥相比,简直没有可取之处。”欲扬先抑,运用得当。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观察之细,惟妙惟肖地把我们熟知的麻雀写活了。
人们的怜惜是因为麻雀熟悉的身影与我们相依相伴,不离不弃。作者对现代都市人与人的隔膜描写到位:“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涌动的人流与车流总是滚起冷漠的烟尘,钢筯水泥时代打造了方便与快捷,也打造了坚硬与隔膜。带着机械印记的单调表情写在每一张交错而过的面容上,闭上眼也不会想错那种麻木,偶尔的一个微笑毫无疑问是来自熟悉的身影,一样的程式化,流水作业的时代,为什么人的表情也都成了复制品?”诚如作者所言,复制、合成、克隆诸多现代手段让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便捷,但心与心的距离,却从来没有过地如此疏远。眼中掠过的精灵,对隔膜和距离进行了拷问:“在这规矩如五线谱一样的城市,娇小的麻雀就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自然的笔触轻灵地挥动,它们那小小的身子起起落落,一篇篇灵动的自然乐章在这城市的天空逸出,惊起树稍的风,溅落花蕊的露。”
作者笔下的麻雀,被冠于“异常可爱”、“最质朴”的美誉。麻雀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季节的变换总会卷走一切繁华,当自然搭建起以萧瑟为主基调的舞台时,麻雀是这个沉寂世界里活泼的精灵。”此刻,“它们灵活地在树枝上跳跃,在阳光中飞翔,在路面上蹦跳,在窗台上轻啄……那小小的影子在视线所及的每一处,冬日里被寒冷冻住的心让这柔软的小东西一点点化了,可爱的小东西,用活泼驱赶着天地间的沉重,带给我们冬日阳光一样的暖意。”四季追随,春秋相伴,麻雀朴拙的忠诚,感动了作者,也打动了读到文字的我。
“总是看到麻雀,每一天。每一个单调的日子都会看到这鸟自由的身影,每一次灰暗的心情都会在这鸟儿轻柔的呢喃中有了亮色,它从不是漂亮的鸟,却是我心中永远不会远离的鸟——不需我去豢养,却时时轻舞在身边,这永远的麻雀!”文章收笔也很漂亮,呼应了篇首,也点了题旨。
读完全文,尤为我称赏的还是作者的文笔。她写麻雀的声音:“那是歌者咏出的灵巧的滑音吗?附着几分轻盈,流畅地划过每一个地方,洒下一串串轻柔的叽叽喳喳,那娇弱的麻雀声在众多歌声美妙的鸟鸣中绝对说不上最动听,但却可以说最质朴,就如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孩子,不带一点修饰的声音稚嫩得如春天刚刚从土里探出头的草芽,让人忍不住秉住呼吸侧耳聆听,好像一个不小心就会惊吓了这柔嫩的鸟声。”她写麻雀的身形:“一只只小麻雀如一个个长了翅膀的褐色小绒球,虽然不漂亮,却异常可爱,在天空中来来去去,在碧绿的枝叶间穿行”,“小小的麻雀在地上如施了魔法的绒球,不,才不是呢,那是灵巧的手指在琴键上舞蹈,起起落落间,水一样的音符从指间流淌出来,谁说麻雀的蹦跳间没有音乐在弹响呢?只是我们的耳朵阻碍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无法去品味自然演奏出的美妙的轻音乐,所幸我们的眼睛补偿了这一切,从麻雀的弹跳出,读出一缕自然的旋律,而麻雀,这自然的手指,只是那么悠然地在一日日的生活中把一切完成。”冬日的麻雀:“此时寂寞的天空中总会有麻雀翛然来去,原本平淡的羽毛在这缺乏鲜亮色彩的世界竟漂亮了许多,或许是秋季的养料蓄积,小小的身子格外圆滚滚,栖息在落光了叶子的枝条上,就如缀上一个个小绒球。它们灵活地在树枝上跳跃,在阳光中飞翔,在路面上蹦跳,在窗台上轻啄……”
我甘受诟病地大段引用,实在是出于不忍割爱。可以说,没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感悟,这样的文字,断难写出。如果说到本文的可商榷之处,我还是想起了季老的教诲:“写抒情的东西,说得太透,反而会产生浅显之感。”冒昧而论,不知东风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