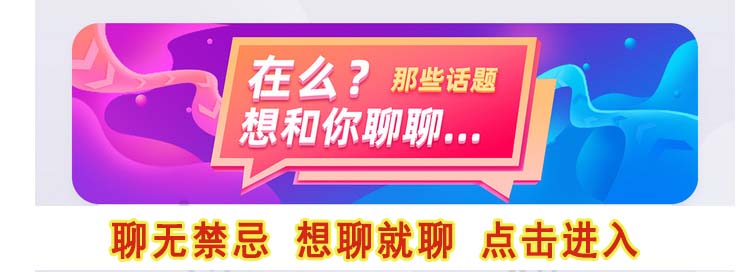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们搬离老宅,已经五年了。老宅的两棵老树,还挺立在那里。
鲁迅先生在《秋夜》中写道:“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巧合的是,半个多世纪来,我老家老宅的北园,确实只有两棵树,确实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一棵乃至两棵上了年纪的树并不少见,不寻常的是那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树所带来的岁月深处的故事。老树的存在,让人心里安稳,人们并不要求老树做些什么,只要它能健健康康地屹立在身边。就像家中的老人,也许已经行动不便,也许已经思维迟钝,也许变成一个爱撒娇的老小孩,但只要家中有老人,心中就有遮蔽风雨的无形大伞,就有疲乏无力之后的休憩之所,就有孤立无援时的精神支柱。
我每次离家外出,都有恋恋不舍的感觉,但我从没跟家中的老树告别,在家时,我总是忽略它,可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两棵立在后院里的老枣树。我会想起老树曾经给我带来的快乐,想起它夏天的绿阴,想起它秋天的落叶,想起它严冬的落寞,也想起它春天时的重生。这两棵树,听说是祖父当年栽下的,比我家大哥的年龄还大。老树的确很老了,每年春天,冰雪融化田野返青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枣树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老枣树只是略微迟钝些,还会发出嫩嫩的芽,还会长出美味可口的大红枣。
童年时期,吃枣就上房去摘,有时从房顶跨到树上,红色的大枣挂满高枝,越是远离枝干的地方越多。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侧枝上大枣特别多,手又够不到,我只有大着胆子,一手攀着上面的树枝,一边脚踩着下面的树枝慢慢向外挪,突然只听“咔”的一声,脚下的树枝突然下垂,原先是斜上的树枝已经变成平的了。我赶紧往回挪,好在枣树枝韧性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房前屋后的杨树、柳树、榆树,都已经消失无踪,随着而来的是荒草萋萋,以及两棵枣树,始终屹立不倒。端午节期间,我们还到老宅枣树下边,拔起几大把艾蒿。俗话说“老屋闹鬼,老树成精”,我家老院子和老枣树也有些这意思。老院子墙皮斑驳,老枣树的树皮也斑驳,里面荒草萋萋,要是外人乍一沓进来肯定会有些不适,胆小的甚至可能会觉得有些害怕。但我每次进去,所感到的只有浓重的亲切,老院子灰头灰脸的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时间在老院子里发生了凝固,停留在了多年前的一个时代。一脚踏进去便会倒跨回一个世纪。
这么些年来,老院子和老枣树就这么默默相守着,相看两不厌,就像大多数的农村夫妻一样,没有琴瑟和鸣,没有山盟海誓,只用最朴素到无言的方式默默相扶,践了一个从未说出过口的相守到老的盟约。老院的屋墙虽然都是老砖坯的,但经久不倒,我总觉得是因为老枣树把根系植入了其中的缘故。
多年来,枣树虽不像大树舍身做梁那般壮烈,却也绝不是苟且偷生,而是活的理直气壮。在困难时期,枣子不再是时令的果子,而成了维系生计的口粮。那时很大一部分枣子尚在青涩时就被打落下来,用作果腹,只有一小部分枣子能熬到发红。当然,在我小学学习篆刻时,还曾经用枣树枝做了平生的第一个印章呢。
当然,上房后上树,在春天也是常有的事。
那时,我家的五间平房,与姥家的三间草房,只相隔着一条东西向的小屯街道,两家类似于前后院,鸡犬之声相闻,无时不可往来。每年开春,我换下穿着一冬的大棉裤、厚棉衣,换上单裤、单衣,顿觉身轻如燕,真想要飞起来。于是就去上房玩。从自家鸡窝棚子上到耳房顶,害得下蛋的母鸡抗议着跳出来。大公鸡也远远的跑来要向我挑战。
我不管它们,从耳房爬到了正房之顶,顿时全屯风光尽收眼底,四面八方豁然开朗,春天的氤氲大地,村屯中的杨花柳丝,劳作的乡里乡亲们,象一幅幅静美或动态的图画。
家乡乃是辽河下游洼地,东望庞家河,掩映在护河林之中,忽隐忽现,有时如镜子一样反射着柔美的春日。西望医巫闾山,尚在百里之遥,象水墨画卷,横亘在太阳暮落之地。
正当我得意观光之际,忽然自北边传来一声声呼喊,那是姥姥响亮的叫声,“小五子,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姥姥是小脚,这时已出门奔我家来了。我惟恐被父母知晓,赶紧从耳房和鸡窝连滚带爬地下来,蹭了一身灰,老母鸡又一次抗议我,大公鸡又来追逐。我一溜烟地从家门口直串入南园子中了。
仿佛又听见了姥姥的呼唤。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五年了。那时,每年的春天,姥姥都会帮我们制作柳笛。身体虚弱的姥姥,望着春天的园子,总会说:“春天来了,好日子来了。”
现在,在对故乡愈来愈怀念的记忆里,这两棵老枣树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圆心。我知道,随着年月的增长,这个记忆的圆的半径会越来越小,甚至会最终小到没了半径,那时,陪伴了我家祖孙四代的枣树便成了故乡赠予我的一个永久的图腾,让我在对故乡的回望中,不至于彻底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