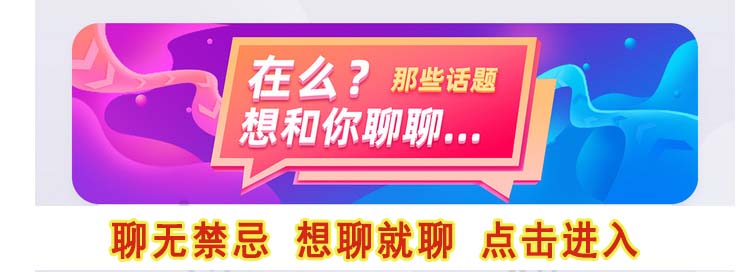电子元件厂生产的磁头都销往了国外,由于产品销路好,生产规模扩大了,今年已经招工两次了。
看着新进来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工。因为工厂生产的产品,工序多,工艺繁杂,又是计件,所以以女工居多,只有机床上有少得可数的一些男工。刚招进来的都是十九、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提着大包小包,扛着行李卷,像是从外地来的。原来的工人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她们的师傅,交谈中才知道她们有的是从农村来的,有的是从本地招的,大学没考上,来工厂打工了。
工厂最早的时候,工人们中午不回家吃饭,厂子里也没有食堂。从外面雇了两个打扫卫生的女工,中午兼顾把工人们带来的午饭给热了。把车间旁的一间小屋腾开,修了一个大锅灶,把饭盒都放在三个大铝笼里,到中午十二点,统一由这两个女工把热好了的饭盒送到另一个空屋里。屋里只摆了几张桌子和椅子,去早了有坐的地方,去晚了就只能站在窗台前,或者靠在墙上,抓紧时间胡乱地吃完,赶紧回车间又干活去了。
在我的印象里,工厂一直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家吃饭。每个工人的产量都是定了的,不是八小时之内就能完成的,手快的也得在晚7点左右完工,手慢的也就得晚上十来点才完工,晚上车间里常常灯火通明。随着工厂订单的增加,工人们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自从来到这里上班,我好像没吃过一顿现做的饭菜。总是前一天晚上做好的饭菜,第二天中午带到厂子里,米饭、馒头得和菜装在一个饭盒里,热好了就成泡饭了。晚上十来点下班,家人早就吃完晚饭休息了,还得吃热了一遍的饭菜。在厂子里能吃上热饭就不错了,有时还会吃不上,我的同事杜丽和田霞有一天发现她们的饭盒不见了,也许是拿错了吧?她俩就想着拿回饭盒,可是什么也没等着。不知是谁把饭盒拿走了,把里面的饭也吃了。中午饭没吃上,时间也都耽误了,她俩饿着肚子上了一天的班。后来,又有好多次,别人的饭盒也不见了。
渐渐地工人越来越多,大锅灶热不了那么多饭盒了,中午带饭的待遇也没有了。有的人在工厂门外的小饭馆,凑合喝一碗面,有的人泡一袋方便面。那时工资不高,一个月就几百块钱,都舍不得午饭花太多的钱,小姑娘们都爱美,发了工资也想买件漂亮的衣服,一两样化妆品。况且吃饭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生产定量完不成,会扣工资的。简单吃些就算一顿午饭了,泡面也不像现在那种桶装的,太奢华了,只有一元一袋的方便面,锅炉里的开水也不是开水,泡出的面就象女孩子的烫发,卷卷的,外面粘里面硬,一点儿也不好吃。
曰子就在每天的面碗里打发了。工厂的产量仍在不断增加,我们每天的产量当然也就在不断地增加。我们是做电子元件的,电子产品里的一只小小的磁头,要经过四五十道工序,才能包装出厂。增加了定量,我们的吃饭时间不得不一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决定办一个食堂。起初,我们不大愿意在食堂吃,饭菜量少又不好吃,有时还得排好长时间的队。由于经常吃不好,又吃得急,我得了胃炎。不能吃菜,一吃就胃疼,常得用手顶着胃部干活。想请假都很难,我们的工作是每个人干一道工序,十几道工序是上下连接的,十几道工序是一个组。如果我请假了,后面的工人就无法连接上了,因为每个人只会做自己的那一道工序,一个人会影响一个组一天的产量进度,组长就要被班长罚。为了全组的人不受牵连,我只好坚持。中午只能吃白开水泡馒头,大概这样吃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食堂的刘姐看到了,问我:“你怎么不到食堂去打饭?”我说:“我得了浅表性胃炎,有时吃菜就胃疼。”她对我说:“以后早上你来了,就把饭盒放到食堂的窗台上,带点儿软乎的饭菜,我十点上班帮你拿进去热了,你中午就来吃热饭吧。”我说:“那不行吧,你给我一个人热饭盒,让别人说闲话呀。”刘姐说:“没事,你有病又不让请假,吃点热饭应该的。”临走时又回头嘱咐我:“明天一定要把饭盒放窗台上啊!”“谢谢刘姐!”我们早晨五六点钟就来上班了,而食堂的大师傅们十点才上班呢。进不去食堂,饭盒只能放窗台上。从那天开始,我又能吃上自家带的饭了,而且还是热的。似乎是享受了世界上最高级别待遇似的,心里特别高兴,是刘姐的善良挽救了我的胃—虽然吃的还是泡饭。
记得是在那年的冬天,中午我急匆匆地赶到食堂去吃饭,一进门就看见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嘴里叼着个烟斗,蹲在食室里间的门口,是谁家来了亲戚?不对呀,他也穿了一个白围裙,和食堂里那几个女同志穿的一样。我也没顾上想,就拿上我的饭盒吃完饭走了。
第二天,那个老头还在。叫他老头,是因为他脸上皱纹挺多,也不知他姓什么。他肯定是来食堂工作的,只是都是女同志,突然来了个老头挺显眼的,而他却不在意。正当我们吃完饭,得去锅炉房打水喝的时候,食堂里是不供应开水的,那个老头突然站在窗囗前大声说:“孩子们,都到这儿来喝碗米汤吧。热乎乎的,是免费的。”工人们正要走,这时都迟疑地停了下来,老头看大家都没过来,只是站在原地观望着,他就把那一大铝盆米汤,吃力地搬了出来,放在饭厅里的长条桌上。工人们相互对视着,有一个人走了过去,他马上递过去一个盛汤的大勺,亲切地说:"喝吧,喝吧,自己盛上,米汤也顶水喝,还有营养呢。"接着又有人走了过去,一会儿工夫,一大盆米汤见底了,他始终在旁边笑着、看着…
饭厅的长条桌上从那天开始,有时有米汤,有时有一大铁壶开水,工人们每天不用嘴里边嚼着饭,边往锅炉房走了。食堂里的饭菜不好吃,不是炒土豆丝夹生的,就是豆芽炒粉条过火了粘乎乎的。工人们工资不高,饭菜成本高了,食堂还得亏本,只能做些便宜的饭菜。最近隔三差五地还能吃上咸菜,不少去外面小饭馆吃饭的工人也回食堂吃饭了。原来,食堂有时采购回来的大白菜、圆白菜的菜帮子要扔掉,老头就把它们攒在一起,洗干净,认真地切好,拌好,专等中午我们来吃饭时,把它们搬出来放在饭厅的长条桌上,这就是我们的咸菜,不知老头怎么做的,还挺好吃,大家叫它"食堂里的小菜",吃得有滋有味的。我不经常吃,因为我的晚饭可以在家吃,比她们吃得好。农村来的和外地来的,不能经常回家,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回去短暂的几天。我不舍得吃食堂里的小菜,也不舍得喝米汤,这样她们可以多喝点儿,多吃点儿,都年纪小小的出门在外不容易。
有一天我忘了送饭盒,九点了才想起来,老头在院子里择菜。我说:“师傅来得真早。”他抬起头来:“不早,不早,我老了,没那么多觉儿,早来一会儿,把这菜叶儿腌上点儿,孩子们爱吃,没有别的调济的,放把盐放点儿味精就成了。这里人多米饭做得多,得在大锅里用水煮几滚儿,捞出来再蒸,剩下的米汤就都倒掉了。我看挺可惜的,就给孩子们熬上米汤喝。有时不做米饭没有米汤了,我闲着也是闲着,就烧一大壶开水,放在桌上你们随便喝。我有时间,也没别的事做。”我听了顿了一下,说:“师傅真好!”他憨厚地笑了笑。
夏天到了,饭厅的长条桌上又摆上了一大铝盆绿豆汤。虽然汤的颜色很浅,显然是绿豆没有多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头给熬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家看到绿豆汤,都不由得用眼睛去找老头,这时准能看到老头蹲到角落里,正抽着他的烟斗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总是躲得远远的,生怕我们哪一个不好意思去那个长条桌前。他真是善解人意呀!食堂里的那几个女师傅依旧是和从前一样的面孔和态度。我们私下里都在议论着、高兴着、幸福着,这是老头带给我们的一种情绪。
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跑着去食堂,食堂里却冷冷清清的,没有了往日里的热气腾腾,而且饭厅里的长条桌上是空空的。我说不上怎么了,心里有种烦燥,工人们互相之间也少了打招呼,吃完了饭都急急地走了。怎么了?怎么了?不知道,都急燥。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还下着小雨,我们都穿着雨披,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好不容易捱到中午的饭点儿,我们迫不及待地都往食堂跑,咦,长条桌上仍然是空空的。所有的眼睛穿过打饭的窗口,寻找那个大铝盆,它在锅台旁放着,没有了往曰的热气,那里曾有热乎乎的米汤,浅绿色的绿豆汤…所有的眼睛在寻找角落里的那个烟斗,没有,都没有。我们一下子失落了,可没有一个人去问窗口里的那几个女师傅们。这一天似乎很漫长,工休时竟没人说笑了,到晚上下班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默默地回家了。
又一个早晨来临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走进车间,当上班铃声响起,第一件事是开早班会,班长简短地安排了一天的生产任务,散会了。班长却破例地坐在我们旁边,说:“李师傅去世了。下雨的前一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李师傅骑着自行车出了车祸。”大家一下子怔住了,那么长时间直到他离去,我们竟然不知他姓什么,总是私下里叫他老头。中午又到吃饭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往食堂跑了,大家走进食堂,不约而同地,情不自禁地走到饭厅的长条桌前,虽然没有了大铝盆、大铁壶,但我们却看到了抽着烟斗的李师傅——那个被我们叫作“老头”的,远远地在角落里抽着烟斗笑着、看着……
李师傅的事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了,只要一想起那个工厂,那个车间,那个食堂,那个饭厅的长条桌,那个大铝盆,那个大铁壶……就想起那个抽着烟斗的普通的“老头”,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李师傅。让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位老人,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