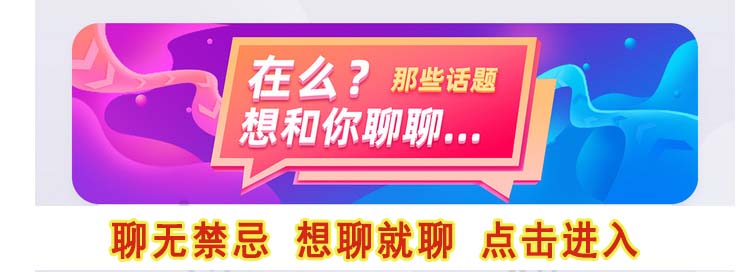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尚在襁褓中的我,没有奶吃,更没有炼乳喝,是“饼角”和桃酥伴我长大成人。从小培养起来的口味,跟随了一辈子。尽管我长大了,不能完全再依赖昂贵的桃酥,大部分时间吃着廉价的自制炒面,可还是有着难舍的桃酥情结。炒面毕竟是桃酥的替代品,聊胜于无。“饼角”是“桃酥”的前身,工艺远差于桃酥,穷日子里,有了“饼角”就非常满足,哪还有对桃酥的奢望?可遇到桃酥,所有的馋虫子又会被勾出来。
我家有个用纸浆制作的小笸箩,外表糊着蝴蝶飞的花花纸,里面盛着我的“饼角”。妈妈常说我儿时趣事,刚学说话的那阵,要“饼”就喊“本”,吃过许多饼,舌头就卷不出一个“饼”的发音来。后来,记不清何时,我的“本笸箩”不知从哪里变出了桃酥,每次一块。从此,我的饭量猛增。从小病秧子的我,居然因有桃酥的滋养,变得无需“惯养”了,解了爹妈的心头之忧。
那时,桃酥是奢侈品,得之不易,就像如今有钱人吃冬虫夏草,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爹和妈闯荡朝鲜新义州,带回一笔数目不菲的钱,除了给祖父购置了房子,应该还有不少剩余。挨饿的年代,爹属于“富翁”,他拿出一百块钱,指着妈怀中的我,说:“下一次血本,再不能把小家伙养大成人,就是老天让我们绝后!”
后来妈就拿着这一百块钱专款专用买桃酥。纸笸箩的糊纸浸透了油腻,妈说,这样就不“走油”了,放多少日子也不变味。
我四岁时,身体还很孱弱,有了桃酥的“酥润”,勉强可以扶着墙角锅台沿蹒跚走路了,妈常发出惊喜的笑,最爱说的一句是“桃酥桃酥,喂饱一头小猪!”这是一位平凡母亲最大的心愿,她希望儿子像小猪一样不挑食,更渴望孩子茁壮成长。
我六岁了,记得这年春天好像特别长,妈说,像漂亮女人长长的脖子,是有史以来最不好过的“长脖子春”,其实,年年如此,只是饥荒让人度日如年,就感觉日子太慢。我妈这样说,是因我的饭量大增,一次要吃两块桃酥,不然就闹腾,她很为难,桃酥常常断顿,甚至我也跟着大人吃草面。家里正房安置了一方硕大的石磨,磨盘宽大,妈踮着小脚在磨盘上揉草面,是花生蔓晒干后一点一点捣碎的“面粉”。我搬来一个“吱呀吱呀”的木凳,踩上去看妈“揉面”,小手抓住了面盆沿儿,脚下不稳,把盆儿掀翻,一碎两瓣,“面粉”撒落一地。
妈顺手拿过扫面盘的小笤帚,攥住把柄,扯过我一只胳膊,揍我的屁股,我没有力气,不能像打陀螺那样借着击打力转圈,还可以少挨几下。
妈坐在地上,哭着数落我:“儿啊,你本来就不让人省心,哪辈子缺德了,和你个冤家找上了茬!有桃酥你吃,你还要干什么,草面你怎么能吃?”
妈席地坐着,边哭边扫那些“面粉”,眼泪滴在面堆上,成了和面的水。混合了尘土的“面粉”,她不舍糟蹋。后来,谈到这段往事时,妈说,有点泥土混进去,牙齿轻轻磨几下,不硬碰硬,也就吞肚里了。
妈把嗷嗷哭泣的我搂在怀里,拍打着后背,掉着泪,自言自语,说尽了道歉的话,然后拿出一块桃酥,我马上就破涕为笑了。
出生才三个月,我就被妈抱养,她不能虐待别人家的孩子。其实,除了没经过十月怀胎之苦,我已完完全全是她的儿子,甚至育儿之苦,胜生母百倍。妈一直心存愧疚,这些不能原谅自己的事儿,在我十几岁时全都捣鼓出来,让我饶恕她。妈哪知道?她每说一次,如刀剜心,母子相拥一起流泪。
专用桃酥钱,没有多少日子就花光了,我还是回到了吃妈烙的“饼角”的日子里了,常常吃了就吐,可爹不能再奢侈一回了,只能无奈地看看走开。我妈说,那时候,她宁可把身上的肉撕一块给我吃……
我最喜欢大姨的儿子“维哥”,那时他经常跑我家来,每次都带着一包或者两包桃酥。进门,我就盯住他拐着的包袱看,直到他打开“献礼”,我的眼也不离开,盯着看他解开纸捻儿系着的桃酥包。每包12块,我学会了数数,就从那时开始的,是“维哥”教我的。他拆一包,拿一块给我,问我,还剩下几块,我知道再也得不到,便跑出去了,炫耀我手中的桃酥,馋馋邻居的同龄孩子。
我希望维哥不要走,可他不走哪来的桃酥?每次他要走,我都扯住他的衣角不准,可想到下次,马上就放开他,在身后一推,放他走。他转身抱起我,亲亲我的脸。我伸出一个拳头,说:“早拉钩上吊了,过几天我等维哥。”
老姨家也不宽裕,老姨夫早就过世了,生活拮据,好在老姨婆家在外面有亲戚,时不时捎点钱接济老姨的生活,她有四个孩子,也不大,知道我喜欢吃桃酥,就隔三差五让维哥来我家,送点口粮。
我慢慢长大了,桃酥还是紧俏货,必须用粮票买,农村人哪有粮票,爹妈跟干供销社的连枝叔相处得好,他总是每月塞两三斤粮票给我们,互相不能礼尚往来,妈念叨欠人家的情。到了秋天就煳好几锅地瓜,然后切成熟瓜干,插在树枝上,挂满院子。入缸上霜以后,大部分送给连枝叔了。
妈逐渐意识到,靠别人接济过日子,总是捉襟见肘。于是,她讨教有八个孩子的“六母”。
“一个个张口的,怎么喂大的?”妈说话变得很轻松,她知道六母也很累,不想说得很沉重,怕给她带来压力。
“一把炒面子就打发了,谁像你那样娇惯着……”六母的话一语破的,妈领着我去跟着六母炒面。
一瓢玉米面,三个手指头揑了几滴麦子面,还抖了几下,才放进碗里,拌匀。
“麦子面就起个黏糊劲,没有大用。”六母不舍得麦子面,说得轻描淡写,找了一个不成立的理由。妈点点头。
六母微笑着,两颗门牙露在外面。她死要面子,从不说自家的日子困难,就连困苦面前的无奈,也要找一个堂皇的借口。初见时,我为六伯娶这样的六母感到不解。可是,自从六母给我看了面相,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大出息,感情的天平就倾斜于她了。其实这话半点根据也没有,她不会相面,更不会八卦周易。后来才知,六母认为,吃了那么多营养丰富的桃酥,脑子一定好使,能不出息么!
六母盛了小半碗炒面,还冒着腾腾的热气。我觉得她很吝啬,怎么就那么一丁点,六母一眼看出我的贪婪,努努嘴说:“怕你吃不惯。”说完用手指头轻戳一下我的脸蛋。
那时,吃不起红糖白糖,都用便宜的糖精。六母从小柜子里拿出一包糖精,把我推一边,拿过竹皮暖瓶,滚出了热乎乎的水,满满一碗。六母露出两颗门牙,努着嘴,吹气半天,再拿一个瓷羹匙,在碗里转圈搅拌。
天哪,我居然一口气喝掉了那碗炒面,妈在一边看得眼睛都直了,苍白瘦削的脸颊上堆满笑容。她解脱了,为发现了桃酥的替代品而高兴。
芳香的炒面带着甜味,钻进鼻孔,直入心底;稠稠的浆糊一般,我不忍弄坏形状,从碗边用嘴吸入。最后举起碗,碗扣住了脸,我把粘在碗底的粥都舔干净了,六母和妈笑得咯咯的。
从此,我一直喝了十几年的炒面。妈总是提前炒好,放进一个小坛子里,坛口用瓷碟子盖住,每天早晨舀几羹匙冲泡给我喝。高中毕业那年,妈加大了炒面的量,早晨上工,妈提前起来把炒面冲好,放在锅台边,等我走过就端起要我喝,天天如此。别人都是空着肚子干早活,我是带着热乎乎的温度走出家门。
我吃炒面,出挑成一个壮实的青年了,与饼角、炒面、桃酥相伴的日子,我称之为“幸福岁月”,工作的幸福也不约而来,1975年,经人介绍,我去一家供销社工作,干办公室文书,兼售货和对外业务。
妈一直怕我饿着,常嘟囔一句:“长个子就得炒面。”家里没有奢侈品桃酥了,我总以为,她是在培养我的口味,就怕我提“桃酥”两个字。我知道家庭经济不允许奢侈,不敢说半句与“桃酥”有关的话。那个盛桃酥的花笸箩还在,油性都渗到了外面,妈时不时拿出来晒晒,我都躲着走,生怕驻足看让妈妈为难。
头天夜里,妈一直到半夜才睡,她连夜炒面,之后又赶制了一个崭新的小花布包。第二天一早她把足有三四斤重的炒面装入塑料袋,然后套上小花布包,系上袋绳,放在了我的行李包里,按了按,说:“记住了,早晨起来就喝,别一忙就忘。”
我的眼泪不是太容易收拾住,听了妈的话,顿时鼻子一酸,眼眶跑满了泪花,一把搂住小脚的妈妈,她差点跌倒,怔怔地看着我,不知所措。
我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拍着妈的后背,我不知妈是否承受得了一双大手的力度,她没有哼,忍受着儿子第一次给她的激动和温暖,体验着第一次分别前相拥的感觉。
她突然推开我,眼睛惊慌地看着我,说:“儿啊,妈没有桃酥给你拿,别怪妈。”
我语塞了,嚎啕大哭起来,妈的头伏在我的肩膀,也不抬起,我享受着母子最激动的时刻。我一生都难忘那次离别的滋味,其实距离老家就是二十多里地,仿佛是越过万水千山了,仿佛一去是经年,或者更长。
妈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过伏在爹肩膀的一幕或者几幕,生活的艰辛已经把女人的这份幸福和浪漫磨没有了,我代替了爹的角色,给妈一个肩膀。我应该给妈一个坚强的肩膀了,那些年爹妈累得已经驼了背,哪有心思互靠肩膀。
我曾经想,在那个时代,也许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有那么一次与孩子离别的感伤,很多孩子一辈子守在妈妈身边,妈妈都期盼着孩子离开自己的怀抱,可又是怎样不舍,矛盾的滋味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尝到,我妈很幸福,儿子可以带着妈妈期望的眼光离开她,她可以踮起脚跟,站在街门旁,举起她的手,与儿子挥别,嘴唇可以翕动,说着她早就想好的话,或许一点用也没有,可对她的心有用,就像一抹温暖的风掠过,一罐糖水浇过……
爹告诉我,干“小伙计”就一个字“勤”,妈却唠叨了半宿,就怕我没桃酥吃不饱,又勾起了我对桃酥的强烈欲望,到了单位,我咽下口水,投入了工作。
我们这些“小伙计”每天要很早起床,先扫供销社门前的地面,然后去“副食品摊”包桃酥。
没有几天,我包装的桃酥就不用纸捻打十字系住了,折叠技术很好,经理夸我说:“小伙子对包桃酥就是有感觉。”也许和那些小伙计也混熟了,那日我“放肆”了一把。
铁箱子底剩下很多桃酥渣子。“明人不做暗事”,我当着大家的面用三个手指头揑了一簇放进嘴里,品品之后说:“真甜,怪不得这样好卖。”
所有人的目光都吃惊地看着我的举动不解,摊点经理也傻眼了。
早饭后,我被罚站在经理的简易办公桌前。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见利忘义”,“勿以恶小而为之”,“干干净净不犯病”……
很多经典道理在我耳畔回响,我惊讶经理说话的水平,竟然可以熟知那些经典文史俚语方言,可这些话如刀一般刺痛着我。
没过几天,我被头儿叫去,他说了些干供销社必须具备的素质条件。我懂了他的意思,含泪卷起了铺盖,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带着我妈妈给我装在袋里还没有吃完的炒面。
我不是没有深刻反思过。
也许贫穷的人就没有资格讲意志力,孟子说:“贫贱不能移。”我“移”了,因为贫穷,因为嘴馋,我不能找借口辩解。岂不知,那些桃酥渣子还要被填充到每包桃酥里,不能缺斤短两。
回家了,妈知道了我被“回家”的原因,默默无语。那个夜晚,她躲进了另一个黑暗的房间,没有点灯,一直在抽泣。
第二天,她将那个油津津的蝴蝶花纸糊的小笸箩砸得粉碎,丢在院子的一角。我不敢面对,心中怨恨桃酥给我带来厄运,导致两个“饭碗”都碎了。回家不过几天,妈妈的视力减退了,看东西要觑觑眼。
是不是我的恨让妈生气了?我没有表露出来,她也不会计较儿无知。那天我站在妈面前好长时间,嘴唇蠕动着,想给妈道歉,更想安慰她几句,可我羞得难以张开口,转身跑了,不争气的我有什么资格!
妈那年是46岁,因为我显得很苍老了,头顶的白发好像几夜就窜出来了。三年后她走了,我还在外地上学。我一直认为,是桃酥惹了祸,断送了我妈妈的生命,从此我不吃桃酥了,理由是,我吃着“烧心”,胃难受。
那年去我的连襟家度夏,连襟的父亲常常和我聊天,说起干供销社,他说自己也当过旧社会店铺的小伙计。他知道我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伤感地说,那时候,他也包过点心,戴着口罩,讲卫生……
口罩可以抑制人的欲望吧,我这样想,心底在流泪。
他露出同情的脸色,对我说:“少年时,可以无知无惧啊,”然后拍着我的肩膀继续说,“也要懂得夹住尾巴,学会收敛。”
那年我17岁,第一次恨自己馋嘴了,也隐约意识到性格里我行我素的任性,很可怕。自我认知的深刻度往往不足,自我原谅仍然掩盖着虚荣。人不能永远不成熟,收敛不住人性的弱点,有些坎儿就过不去。
桃酥,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直到多年以后,我初为人父,才体谅妈妈的一片苦心。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妈妈不惜巨额金钱,用她所有的爱,呵护我的成长。无数次夜深人静时,我抚摸着照片中母亲的脸,禁不住泪流满面。
肚子里再也没有了那个馋虫子了,想起饼角、炒面、桃酥,就想起了妈妈,想起了成人的艰难,懂得了一点做人的道理。成长很不容易,我有过教训,也懂得了“知止”的做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