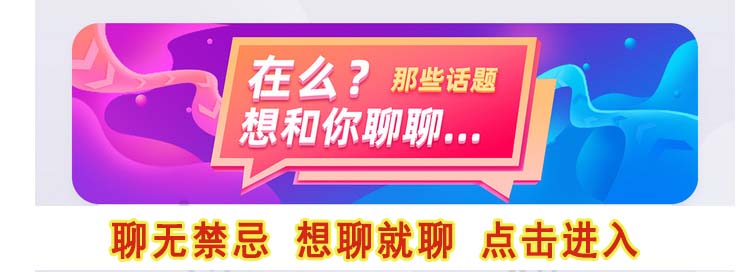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与刘郎,有个约期。
每年乍暖还寒,春天仍在若有若无间,“他”就要来了。
对,刘郎就是桃花别称。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刘郎称它,无论源自《搜神记》还是刘禹锡,听起来都像是穷酸文人编织的妄念。但它也许不介意,娇俏的容颜,总让人想起女驸马,或者祝英台。只要年年能见到它,我宁肯喜欢那句“前度刘郎今又来”。
爱恋刘郎,只在心里,说不出来。
桃花,可以入诗可以入文可以入画,唯独说不得。“桃”只一字,引多少美丽遐想;花开一季,费多少笔墨篇章。千百年来争议纷纷,却越发繁盛。清风随意翻书页,古诗词里桃花翩翩,年年紫陌红尘飞扬。后来,越来越多的书以她命名,或拿她说事,如今的当红作家,没写过桃花倒是奇怪了。
再后来上网,猛然间看见铺天盖地的桃花,男人,无论书生剑客,女人,无论烟花贤良,上到皇家朝臣,下至平民浪子,生点儿事,都拿桃花作底子。春色满眼,几乎被吓住。可怜花开花谢,招来如许是非。
也曾想过,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我喜欢桃花,总得有点特别的原因吧。
想不出来。知道她不是最高贵的,不是最美丽的。木棉花枝高,攀不上的人只能景仰;玫瑰长刺,小心翼翼的人倒更加看重。荷知道开在水中央,梅知道借一缕寒香。只有她,什么都不懂。因为懵懂,倒更显得天真。
她轻白淡粉,一颦一笑,枝头地下,我都觉得极美。所谓痴,也就是为她,也就是这种境界了。
我对她一直念念,自从初见。
那是烟雨浸润的清晨,竹篱茅舍边,白墙黑瓦前,三两棵粉红桃花随意散落。在最深的俗世里,绽放最清逸的姿态。没有华贵气,没有凄凉味,红尘里单纯的喜悦。
想起胡兰成一句:“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她静。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我讨厌胡的为人,却不得不赞同他的眼光。烂漫的是形,安静的是心。
自然,自在。无心,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