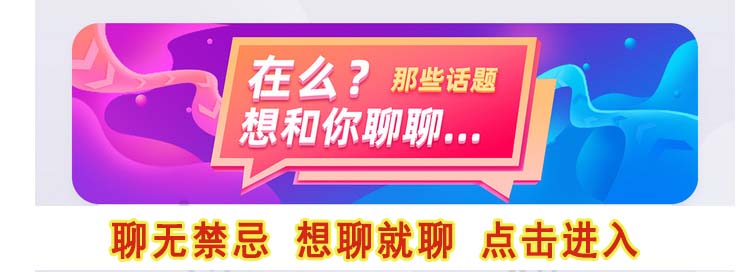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是一个通渭人。我奶奶79上没死,硬是活到了和毛主席一样的寿辰。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她慈目善眉,和蔼可亲,我们是几个孙子经常和她睡在大通炕上,听着她讲古今长大。虽然我三岁时就答应长大了给她纳一件红裤子,但我对奶奶总是敬而远之,亲热不起来。这主要根源于她在六0年晚春的“自私和冷酷”。
那年春天,青壮年都去“洮河工地”,我奶奶的四个儿子去了三个。家里就剩下我奶奶和他的童养媳———我的二婶娘和四个孩子;我婶娘的大女儿和我的嘎叔同岁,都两岁了,由于挨饿走路都不攒劲。我的姑妈稍微大些,也就是五六岁,还有一个我婶娘的小女儿,还在吃奶。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面对家家关门,户户死人,饿殍遍地,满山遍野没皮的榆树,奶奶作为一家之主,决定举家外出要饭。但是两个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女人,要带四个孩子,而且三个不会走路,难度可想而知,几经掂量和踌躇最后决定:一起外出,通路要饭,孩子各带各的。这样,我二婶抱上吃奶的小女儿,给熟睡中的堂姐留了一口榆树皮的熟面一碗凉水,因为小脚的她无论如何也没本事带走两个孩子,抱上大的更吃力。我奶奶抱上儿子,牵着女儿出发了。
这一家五个人延现在的靖天公路向西南乞讨,一是大路安全,不害怕打劫贼,风传有人抢别人的孩子吃肉哩;二是他们听说鹿鹿山有汤喝。到了第三天早上他们在过夜的涝坝里喝了点雨水,吃光了要来的最后一把榆树皮熟面。起身上路时,奶奶再也抱不动自己的儿子了,只好把他放进一个土坑里,希望过路的收留他,其实也就是遗弃了,那年月谁还有能力收留孤儿啊?有儿子的绝后的不少了。
四个人继续走向鹿鹿山——那心目中的圣地。到了中午,他们来到了庄子梁上,其实也就走出了一两里路。一辆吉普车停在了一家人身边,婆媳俩吓得发抖,以为遇上了打劫贼。没想到车上的人抱下了我嘎叔,问是不是她俩的孩子。为了舍一活四的讨饭大计,婆媳俩异口同声地否认了。公家的人鬼的很,指着我二婶怀里的孩子说:“这两个娃娃的项圈一模一样,你们口里说不是,眼睛里在认了。”我二婶被迫无奈只好说,孩子是婆婆的,为了活命我奶奶死不认账,硬说孩子是我婶娘的双胞胎。
好在来人态度还好,说:“谁抱上这孩子,就给谁些馍馍和几斤小米。”奶奶人下了亲儿子,拿到了干粮。来人还说,赶紧带着孩子回家,救济粮三天就到,他们是负责沿途劝人回家和临时救助的,再也不会叫活的饿死啦。车上的吃的不多,只给他们两斤小米。
经过五天的磨练,我奶奶为首的要饭壮举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我嘎叔幸运的活下来。可怜我没见过面的堂姐无辜地饿死了,二婶回到家,孩子已经从炕上溜到地上,爬到门后头,哭睡着了,醒不过来了。令人揪心的是孩子没吃那口榆树皮的炒面也没有喝水。
现在我知道了,奶奶也是孤儿,姓氏不详,随了她当丫鬟的义岗薛家姓薛。五九年我爷爷饿死了,他守寡40余年,养儿育女,持家度日。他那样做,大概她更懂得怎样度饥荒吧。但这是我心中永远不能抹去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