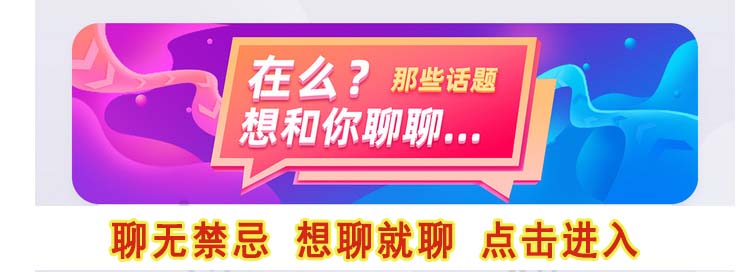最近老觉得不舒服,慢性鼻炎又犯了。鼻子里满满地,似塞紧了棉花,呼吸急促,每每睡下总要用嘴来呼吸。整个人也憔悴不堪,深皱的眉头有着不属我这年纪的忧郁。前些天听见有人因慢性鼻炎而去了,心里颤颤地,经打听原是撞了个有鼻炎的老人,心下才安静些。毕竟我还未断绝尘念,对未来也充满憧憬。一直以来都很痛恨慢性病痛,“士可杀,不可辱”,哪里容得它这般折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65天的零头是在与病魔战斗,有时还打“加时赛”,在经历过“尝百药”后健康才得以收复。
我这慢性鼻炎有七个年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关于这位老友的事还得从初二时的冬季运动会开始说,也就是六年前。
零三年对我来说可谓是悲喜交集。那年的冬季运动会班上参加的人极少,班主任大发雷霆,命令班干部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后果自负。我参加了立定跳远,意外地夺得第四名。学校张贴红榜,我的名字是最后一个。虽然如此,但是那毕竟是我第一次上红榜,心里美滋滋地。鼻炎悄然而至,鼻水开始流个不停。同学说我第一次上榜“感动涕流”。但我有种预感,今后的日子会更加流涕。
事情爆发时我的鼻头血红,浓黏的鼻涕如两条泥鳅,在鼻腔内外进进出出。
终于挨到了星期六,父亲很着急,放下生意领我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求医。医生简单检查后说是鼻炎,拿起笔在纸上龙飞凤舞了一会。父亲又带我到姑父的诊所,又是一番检查后确诊为慢性鼻炎。事后到药店买了二十块钱药。父亲说:“好的医院只适合看病,不能买药”。
鼻炎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都不能吃,除了米饭和药外。同学见我天天用药,忙来问故。我如实相告。之后的日子里很无奈。早晨起来室友问:“病好了没?”服药时有个声音在喊“吃药呀”,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也不用“吃饭了没”而用“药吃了没”。 仿佛一夜之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在吃药。最后我只得偷偷地吃。大约半个月后鼻炎好了,但箱子里面也满是瓶瓶罐罐。之后不论去哪里母亲都让我随身带点药,以防万一。母亲的忧虑没错,好几次病发都幸亏有药在身边。后来我便有了个名号“药王子”。
没有鼻炎的日子里很愉快,和常人一样什么都能做都能吃,抽烟喝酒样样俱全。时常在想,假如没有那病该多么好。
高一时期重点班的一位女同学因鼻炎演变成了鼻癌,全校的人捐款救治。我把好不容易抠出来的十块钱给了她。听同学说她很可怜,原本漂亮的她头发掉得精光,呼吸极困难,喜欢言谈的她也变得沉默,整日以泪冼面,总之要有多惨就有多惨。我很同情她。从那以后只要旧病复发,我就会想起她。我开始有危机感。我把这事跟家里人说了一遍,可惜没能引起轰动。
高二时的某一天旧病复发了,病情较以前重。我明显地感觉到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整个天随时都要倒塌下来一样。我想我完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开了点消炎药了事。我坚持自己的感觉,并央求医生开中药,因为对西药产生了抗体。中药的味道虽苦但见效快,果然鼻炎很快就好了。父亲舒了口气,但还不是很放心,要领我到韶关检查。 在那时韶关医院的设备和技术都是最好的,一般县里解决不了的病痛跨省到韶关准好,但收费也相当贵。看来父亲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鼻炎。我说下次吧,也许吃过中药后就全愈了也说不定。父亲起初不大同意,但终究是拗不过我。
经过了三年的风风雨雨,早已习惯了鼻炎带来的痛楚,心都麻木了。有时候觉得这鼻炎像个定时炸弹,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有时候我感谢这鼻炎,是它让我懂得了怎样去“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人生苦短,快乐一秒是一秒,待到忧愁时再愁吧。
记不清哪天又听到了什么煤矿发生特大事故,死了几个人。近日得知重庆某煤矿发生特大事故,造成30人死亡。
“他们的慢性鼻炎也犯啦”我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