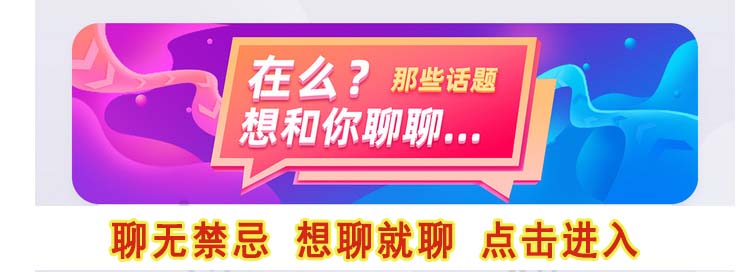这是个没有泪水的春天。你的存在使我渐渐明白,十七岁的花祭,不过是前世今生的一次相遇。因为春暖,目睹了花开。因为花谢,流星才飞逝过夜空。
这个春天已经死在了愿望里。
得知你离去的那一刻,仿佛有一块沉重地巨石呼啸着就砸在了胸口。那种来自遥远异时空的陌生突然就盘踞了大脑,无法思维,无法呼吸。
唯有窒息。
天空为何这么暗,声音怎么变得那么的遥远。遥远得让我们的心撕裂开,无数双手伸进去拽拉撕扯,一道道一条条地碎了。然后又紧紧地捂成团,象铁毡上赤灼的铁一样的被捶打。不停地捶,不停地打,直至千锤百炼。
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心痛是这样练成的。
可是我们不明白为何老天会如此的安排,既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为何又会眼睁睁地从我们的眼底消失。
十七岁,花一样的年少。还未来得及雨露灌溉就已经是花祭了。
无数扇门从记忆里一一开启,又一一封闭。
那渐行渐远的回眸一撇,已然成了永恒。
再见。再见。再见。竟然是永生的不再相见啊!
窒息,除了窒息还是窒息。就像是黑夜里的那些不可名状的恐惧,牢牢地锁住了。耳旁的风呼啸,那种蓝色的气息象针一样钻入脚底心,然后开始漫无边际地游走。
时光停滞在秒针上,我们无法真实地看清眼前,一大团一大团温热的液体注满了泪腺,眼睫毛象筛网似的兜住了汹涌。天空从模糊里开始沉落,一大片一大片的记忆惊叫着瞬间枯萎……
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散漫的,对事对人或许对待感情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这一刻所有的都沉寂了,我们觉得堵得慌,胸口的大石似乎有千万斤沉重。越来越多的脸开始出现在窗口和门前,是那么的静默和茫然。
我们迈不动腿,甚至张不开口,却感觉到冷,从骨质里散发出的冷,彻骨锥心。
已经忘记怎么去悲伤了,死亡就像是一颗耀眼璀璨的流星托着长长的彗尾缓缓地划过天空,然后就砸中了我们,砸的大家目瞪口呆惊惶失措。
与其说被死亡震惊了,还不如说我们是被震撼了。我们就是在缄默中以一种茫然无措的姿态,来面对死神的降临。
最初的呜泣是从一小撮人群里开始的,很轻微很轻微,就像月光下的一滴清泉,一滴两滴,然后是无数滴化成涓涓溪流,在一条一条汇聚在一起,响成一遍遍哗哗地水声。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的悲伤了,呜泣从最初的点滴演变成肆无忌惮的嚎啕大哭后,眼泪的力量冲破了死亡的窒息,就像是绝望中的落水者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嚎啕的眼泪成了唯一可以抒发悲伤的标志。
泪水张牙舞爪的流过一瞬间就开始苍老枯萎了面颊,大颗大颗地砸向尘土飞扬的地面。嚎啕的大哭声和死亡的气息宛如黑夜的巨大羽翼,极速地煽动冲出门外,一路沿楼盘旋,弥漫了天空。
死亡蒙蔽了双眼,悲伤左右了我们的意志,失去是让我们走向极端的罪魁祸首,而一切的根源在没有理智后,我们把它推向了校医的误诊。
这个被死神和悲伤笼罩了的校园开始焦灼起来,成群结队的861就像疯了似的在校医务室和整个校园里乱窜,悲伤被愤怒取代,暴戾象毒草一样的滋生。
或许,只有发泄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不再悲伤的一剂良药吧。
那一片校园在夜半两点的灯影里,静得让人憔悴。
夜风缓缓地抚摸过梧桐树的叶梢,把影子拉得如同缠绕在我们心底的思念一般的绵长。那些不被目光所能企及的暗里,液状的露一点点汇集成晶莹,在一叶嫩白上滑落,湿了一地的硬白。
这个夜晚,星星和月亮都不肯睁眼了。
月光花没有开,狗尾巴草在宿舍楼前的荒草里睡着了。白杨树是个孤独的守望者总是在清寂里站的笔挺,依如那种参天的形象。
我们躺在黑暗里的床上,躺在一片悲伤过后的悸恸里,脑子里什么都想不起,什么都记不住。只觉得黑暗里有只手掐住了脖子,就要窒息的时候,又没有了。然后是静,那种可以清晰听见卫生间里滴水声的静。连一些屋角缝隙里的油虫的爬动声都会钻进耳膜,我不想说又出现了幻觉,也不想说是种错觉。可是黑暗里就有轮椅滑动地声音,那仿佛就是一种寂静里的漫步,一阵阵的有,一阵阵的没。
那时候我们也弄不清自已是清醒的还是迷糊的,总之是处在高度思维的混乱中,感觉来得实在太快,思维跟本跟不上这种节奏。许多的时候是思维来了,感觉已经过去了。而另一种感觉很快地又插了进来。
这种状态的经久持续让我们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上下铺在寂静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尖叫声,这种尖叫是如此的惊心动魄。它就像是儿时的我们对黑夜的恐惧一样显得不可名状。
黑暗中一根火柴划过硝纸的火光,刺痛了我们的眼,这种瞬间存在的光明,又一次让我们感悟到黑夜比白昼更真实的景象。无数个景象在似睡非睡中被放大了。
四周的天际间翻滚着夜色,我们能感觉到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阳光。在那些光的边缘落雪和蝉躁同在,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很长时间都停留阳光下,阳光的气息在他的身上欢快地流动,他的微笑如同和煦的春风一样张扬。然后景象开始摇晃,少年在阳光下逐风奔跑,脚掌有力的蹬在泥土里,随着脚步的起落,泥土和青草象被犁过一样的翻卷开。
无数的蜻蜓突然就出现在黑暗与光的边缘,随着少年的奔跑蜻蜓就似炸窝的马蜂成群结对的奔向了阳光,在那一片光彩夺目的耀眼里,死亡如同雨落般至天而降。
我们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喉咙中仿佛有种咸腥的味道,一大团的粗麻缠紧了我们的声带,我们在绝望中空洞的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的呼喊声。
而那个阳光下的追风少年也宛如落进了慢镜头,在光的黑暗边缘他努力的挣扎着,痛苦得就像撕裂的那种感觉一道道在稚气的脸上堆彻起来。那个暗的边缘仿佛有道质的阻拦。少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冲破阻碍。这样的画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少年的表情随着后退而逐渐模糊不清,而那道就像犁过的翻卷在少年的脚前不断的愈合,飞落的蜻蜓之骸,铺满了那道翻卷。
一双孱弱的手就这样伸进了梦里。其实梦里我们更能实现自已的愿望,竟管是那么的缺乏真实性,但只要一闭上眼一切都可成真。
相见为何那么难,难到起点又回到了终点。
那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群体的悲哀,或许我们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后的相见一面。
在黑暗中努力地睁大眼,努力地不再悲伤。然后在点燃的星火飞舞里去看看那个兄弟离开的地方,在一方故土的宛如隔世的祭奠里说声:兄弟,保重。
也许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或是想做的。
命运总是和我们开着无谓的玩笑,却一不小心成就了我们生与死的相望,阴阳两隔。只有等到记忆如灰烬的时候,才知道你是砍在胸口的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