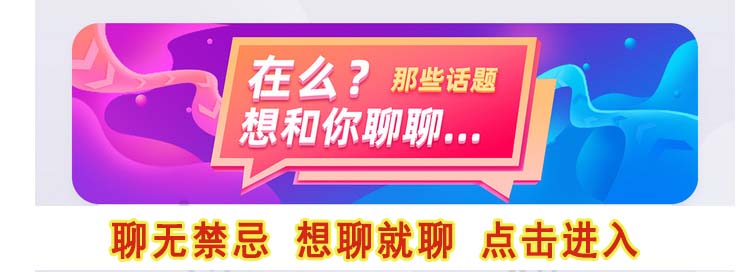词题标明的湘东驿,在南宋时属萍乡县,即现今江西西部、靠近湖南的萍乡市西。当时是比较闭塞的山乡。考作者范成大一生行履,这首小令大约作于1172年(乾道八年)冬作者调任静江知府(治所在今桂林市),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越岁之后途径此地之时。此前几年,作者曾奉使出行金朝,归迁中书舍人并任朝廷史官,接着因对朝廷用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辞官引退归苏州。作者政治上不得意,心情抑郁,这时接到调令,首途广西,来到了荒僻的湘东驿。旅中的孤独凄凉,难以排遣,不禁回想旧日京中故里的友人,忧从中来,写下了这首小令。
上半阕首句点明了客行所至的地点——湘东驿,“忽到”二字,便有非所预想、难料今日的意味,可见远迁广西本非己愿。然而“岂不归怀官有程”(陆游句),官事在身,明朝不得不继续前行,进入潇湘(湖南二水名)之境。“真是”二字,透露出“不意至此,居然至此”的感慨和怅惘。作一个公忠体国的正直官员也是身不由己,乃至不容于朝。作者并没有交待迁官的具体始末,仅从自惊自叹的感喟中表露出微弱信息,供读者去联想得之。怅望苍茫晴空中的重重云彩,意识到自身的所在,距三吴故地是那样的遥远。“几时逢故人?”作者此问,充满了怀旧的情思,也反衬出客行的孤寂境况和失望的悲哀。
江南本山明水秀之区,但对辞乡远别的孤旅来说,一切美景均同虚设,无意观赏,这与荒凉的塞北便无区别了。下半阕首句便发出了如此沉痛的表述:“江南如塞北”,更何况交通阻塞、音书难通,连鸿雁的踪迹也稀少而不易见到。那么,这暮春三月,面对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岂不更令人孤苦难耐吗?通篇就这样由境触情,由情而忆,由忆而感,由感而悲,倾诉了远别的伤痛、怀旧的积郁。两阕之间,过度自然,浑然一体。语言朴素明白,毫不费解,却又含蓄曲折,意蕴深沉,称得上是洗尽铅华、反璞归真。说它道出了眼中景、心中情,意中事,是“人难言之而已易言之”,是不为过分的。
惨惨堂前紫荆,飞飞原上脊令。桓山之鸟,欲去而哀鸣。
苦哉远征人,陟山望亲还望兄,嗟嗟行役万古情。
彼少年者,色何黯然。娶妇未三月,昨来黄纸到官,行将出戍南滇。
归告阿母,阿母叫天。新妇口噤目眵,伥伥不能前。
小弟前致辞,母兄且勿悲。阿母生我二人,兄今有嫂未有儿。
何得远去,存没未可知。弟当代兄役,门户兄自主之。
阿母兄嫂,闻言泪下如绠縻。大兄前致谢,此事甚非宜。
感君区区怀,我心已再思。熟知此别异苦乐,何乃反累吾弟为?
切切相劝止,但言兄嫂勿复疑。翻然出门去,意气何慨慷。
别我先人墓,办我行子装。佩刀三尺馀,挽弓三石强。
弓刀及戎服,罗列东西厢。亲戚走相送,酌酒歌同裳。
晨兴拜堂上,骨从相悲切。临行嘱兄嫂,欲语复呜咽。
但得兄嫂一心善事阿母常喜悦,万里羁人慰愁绝。
收泪就长道,关山别思重。白日结愁云,至情感苍穹。
之子识大义,行当早立功。归报皇帝陛下,无烦远顾蛮中,扬名史册垂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