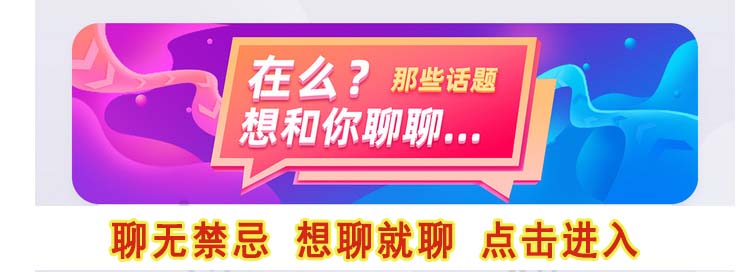因为牙病,早餐吃得很慢,让家人逮住机会说些家长里短。隔壁远房表兄阿生送来请柬,他要娶儿媳妇了。阿生长我几岁,在家排行老幺,我小学二年级时,他大概初一还是五年级,记不清了,那时候村里的学校是有初中的,建宝叔就是初中部的老师。那个冬天,中午放学,许多大人小孩趴在大队一间公房的窗户上指指点点,说是阿生关在里面,因为他对还没上学的小静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小静是文忠的妹妹,我们住的近,四五个人常一起玩,人很犟,脑子反应有些慢的。阿生裹着一床破棉絮,面向墙壁躺着,我感觉他有些发抖。过了几天,学校把我们集中在操场里,贫下中农代表宣布把流氓犯阿生带上来,被两个扎腰带民警拎着的阿生惊恐地看着满操场愤怒而欣喜的红小兵。我们就受到了教育。民警给阿生戴上手铐,三轮摩托车呜呜叫着把阿生带走了。然后高年级的正莲上台唱歌,依稀记得是主席伟大战鼓咚咚红旗招展的意思,最后一个拖音难度很大,类似于青藏高原。正莲的舌头拉得很长很长,让我们羡慕得要死,她弟弟正法和我的友谊也与日俱增。大会以后我写了一篇批判阿生的文章,受到老师表扬,一直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
阿生回来时,红小兵变成少先队,我上高年级,在这个学校有些话语权了。每次看到他,总觉得挺别扭的。阿生个子长高了不少,没再上学,去做了放牛娃。牛倌里也有比他小的,但人人都可以使唤他,阿生那时很胆怯,牛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雕”,隐含羞辱的意思。阿生二十多岁的时候,很少有人再叫这个绰号了,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渐渐找回自信。包工程赚了点钱,建房娶妻生儿子,很红火了几年。后来他沾上,起起落落的,婚也离了。几年前阿生娶了小静的阿姨,日子又慢慢平和起来。不晓得嫁到外地的小静会不会给她阿姨拜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他们兄妹的消息了。即将要结婚的应该是阿生和前妻生的孩子吧,我不太有印象。
说到文忠,他应该是我弟弟最要好的朋友了吧,甚至有时我会嫉妒他们的交情。文忠和弟弟老是在一起“掏野债”,总有人到家里告状,本地方言叫“告消罚”。我对妈妈更喜欢弟弟有一些愤愤不平,只要有人来“告消罚”,我就很得意,你们看看,到底谁更“甜咂”(听话),哼。
有一次文忠和弟弟把学校乒乓桌的铁网架拆下来,在走廊玩打仗的游戏,弟弟不小心把架子扔向玻璃窗,砸破了一块,一溜烟跑了。老师来追究,我心咚咚跳着,犹豫了几秒钟,还是告发了,当时感觉是大义凛然的,只是心疼妈妈赔的5毛钱。如果弟弟还在,我也许不会老为这事纠结,也许能补救,也许弟弟根本就不在意了。弟弟受罚时的情景让我想到少年阿生被拎上台,而且告密者是他亲哥哥。弟弟很倔强,他应该不会伤心,但一定会恨。关于这一点我只是猜测,已无从明了了。
搓了搓手,起身,和妻去探望外婆。感谢阳光明媚,给我一个宽松的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