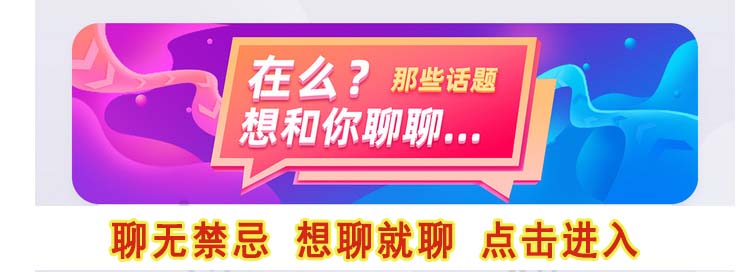时至今日,在中国,“情人”二字在部分人心目中依然暧昧。回朔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恋人不管心里有多火热,只要在公众场合见面,彼此都显得很拘谨,表面上,很难看出谁和谁是一对恋人。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扣上“低级趣味”、“资产阶级小情调”之类的帽子。
记得上小学时,一次学校组织上山开荒,由一位男老师和一位女老师当领队。平常在学校难得见他们说话,可那天他们虽位居队列的一前一后,却是“哎”一声来,“喂”一声去,说得不亦乐乎。懵懂的我们觉得这“哎”“喂”之声挺有意思,也跟着“哎”来“喂”去。两位年轻老师——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是一对“情人”,每当听到我们戏谑的“哎”“喂”之声,脸上不由自主便飞出一片绯红。
到80年代初,恋爱中人依然不敢显山露水,见面时,依然象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以“同志”或战友相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住我隔壁单身宿舍一位叫清明的男老师,和另一位叫如茵的女同事好上了,她一上完课就到他那儿洗手,总听见她敲着他的房门叫道:“清明同志,在吗?”一听到她甜美的声音,门就开了,清明一本正经地说:“如茵同志,是你啊,有事进来吧。”明明是一对恋人,可每天总是“同志、同志”地喊着,我觉得怪有意思,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直到她嫁给他的那一天,校长主持婚礼还说:“今天,是清明同志和如茵同志结为连理的大喜日子,我衷心祝愿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同志永远幸福。”我在心里说:“切,明明是夫妻,一对老情人了,还是什么同志同志的,不地道嘛。”
进入九十年代,过“情人节”已经很时尚了,相爱的人大概没有谁弄不清一支玫瑰、两支玫瑰、三支玫瑰的含意的。在那一天,大肆张扬的“情人”不在少数,“情人节”被过得花样迭出:有大把花钱空运鲜花的,有举办烛光舞会的,有吃着西餐听着萨克斯说情话的......当然,手头拮据的人自然只能小打小闹了。
千禧之年“情人节”那天,我路过一家时尚发屋,见店门口有对搂抱着的男女。可我怎么也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他们不配啊!远看时,那男青年头顶上有一大块疤痕。走拢去,才知道搞错了,原来那疤块是染在发上的一个“情”字,女孩的发辫在头顶绞结成一个“人”字。我了悟,原来“情人”关系在年轻人心中,是可以如此充满创意、充满光亮地摆在明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