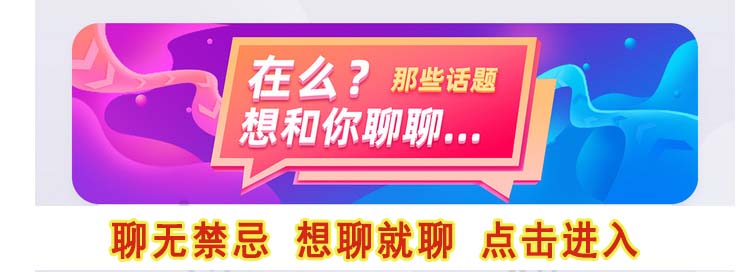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侯,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章好,坎坷一生的王道乾先生译笔好,我每每读及此段,文中这种直攫人心的沧桑和悲凉都会令到我无法自持、谴绻而泣。
是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留住的。这些我们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轻,就让它们自己随风哀哀而逝吧。
"叮呤呤……""老师窗前有一盆米兰,娇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它不象……"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歌声明亮而清脆,我们都还是老师们辛勤培育的那娇小的花。对了,那是我们一本正经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那一年,我初三刚毕业就被保送上了本校高中,其中我还跳过了初二年级,学生做到这份上,也算是没有愧心。在一个闷热的午后,他来了,要借本初三代数,没让他进屋,将书借给了他。他和我同校,今年刚高中毕业,家住在我外婆那个里弄。下午,他将书还回,说35页里有一道题,让我看看。他的样子显得非常地紧张和局促,手里的书就象是块烫手的山芋,塞给我就匆匆地跑了--整幢楼回荡的都是他那连跑带跳急促下楼的咚咚声。我翻开书,里面有封信,字写得非常认真,字迹也很美,记得每年发过新书,外婆都会替我包书皮,他就总是过来替我写名字,他的字写得漂亮,在里弄里名气蛮大的。对了,这是封情书,至于内容我真的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事隔多年,我读过无数情书,而因我惊慌失措,以至于上面的内容竟然记不得一个字的,只此一封。晚上,我将这封信交给了我的父母。之后,我一直不愿意上外婆家玩,直到他家搬走。
上了高中,不断有同学写信给我,后来,为了不影响学习,我几乎都不拆开。好在,父母同意替我保存,也算没有冤枉别人的一片心思。我的课桌里常常会出现一只大红苹果、一个美丽卡片、一件小小礼物什么的,后来,我给课桌加了一把锁。其实,少年的情怀初开是无可非议的,但我知道,他们见着的只是我的一面:在老师的宠爱下,学习不错,年年三好,他们觉得有些钦佩;我受过舞蹈训练,一直在学校舞蹈队领舞,大节小庆时都很风头,他们就觉得我美丽;我练钢琴,常代表学校滥竽充数的去表演,他们就觉得我高雅;我生性有些沉默和懦弱,我们就觉得可亲可近,完全可以大胆地一表心意。当然,另一面是他们见不到的:我虽然年纪小小,但我世故、骄傲、十足虚荣、非常自私,特别不讲道理和不尽人情,有些想法还有点龌龊。看着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空洞的情书,我难以想象他们知道真实的我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随着功课越来越紧,想保持住我的名次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我那多少有点的少女惆怅也在无尽的习题里错过去了。
不久,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刚进校不久,就听见外文系的女孩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他,原来,他念这个学校的建筑系,不但和我同校而且已经是个校园里闻名的倜傥大才子了。我回想起他那天紧张局促的样子,不由暗地里想摇一摇头:这世界变化快。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时是抒情时代的校园,物化的概念就是知识、音乐、诗歌、爱情、吉他、饭馆和啤酒。比如我吧,一进校门就遇上了大学生艺术节,没来得及认识班里同学之前,就去学校里跳了两个多月的舞蹈,是一个去参赛的叫"红岩"的小型舞剧。领舞的老师排练时做大跳,脚扭伤了,她和其它老师在演员里挑来挑去,最后,很不满意地挑出我来领舞,由于年轻,又减掉了一些难度动作,我竟然领了下来,节目得了个一等奖,我也得了个演员一等奖。江姐的大幅剧照就上了报纸,电视台又做了专访,当然,几乎都是领导和老师说谎的镜头,我已经没太有兴趣对媒体说谎了,因为说过之后,自己会觉得很扫兴。于是,我对老师说我紧张,老师就说:那你尽量少讲话吧,六个纸条讲三个吧。前车之鉴是上中学时,有一次被评为全市的三好学生,我那被班主任修改过的讲演稿和报纸上的事迹,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假的,自己看都觉得害怕,看着那些准备认真学习我的读书方法的同学,滋味非常复杂。父母藏起了报纸,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愿意亲戚朋友过多谈及此事。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舞剧里,我一脸隆重的油彩和汗水,再做些夸张的不屈不挠的动作,活脱象个悲愤填膺的疯子,若是让小孩子见着了,一定会被吓得大哭的。回到班里时,同学们都喊我"班头儿",原来他们出于不了解的缘故,选我做了班长。但第二年改选时,同学们明白了,原来我不但不爱管事,更甚的是我还有个不爱开口讲话的毛病(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多数话都是没用的废话,说了不如不说),当然,我落选了,但我心里却很满足。可是,系里和学校又决定让我做学生干部,你看,生活就是在不断地愚弄和被愚弄之中,渐渐地我越来越想离开生活这喧嚣的舞台,更想选择做个真实的观众,想生活在生活的边缘。我知道生命中那最为宝贵和幼稚的热情正逐渐在我生命里逝去,也许这就是开始。后来,读到六十年代的巴黎青年将"生活在别处"的口号刷得满大街都是的时候,我真愿意米兰。昆德拉能给我们上政治思想课。那样,高年级的同学就不会付出如此的代价,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理想主义者。
这个学校里,外文系的女孩子最多,而且洋腔洋调的别具风采,有些异国情调和反传统,比如,每逢元旦学校汇演,我们系,反正我那四年第一年穿日本和服跳伞扇舞,第二年是非洲土著风,第三年是拉丁恰恰,第四年是舞剧卡门,当时的世风里,假洋鬼子般的反差产生美感,所以,深受其他系学生的宠爱。那我们班里的男孩子,一共只有5个,每次班里举办晚会,要让他们出席的话,就必须谈判:我们要清场!别紧张,就是让其他非本班的男孩子退出。开始谈判挺圆满的,后来,随着要带男友出席的女生越来越多,谈判就破裂了。建筑系是一个充满才子的地方,学科的性质理论上需要灵气、创造力和博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很多学生美术功底了得,于是就有了些艺术气质,也是这个学校女孩子们暗暗倾慕的对象。我相信建筑和音乐是相通的,有道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好象跟英语关系却不大,不过,比如吧,我们寝室晚上熄灯后,十天有八天都会谈及建筑学。因为建筑系的同学隔三叉五的就会邀请我们参加联欢晚会。那时西风渐进,新鲜的感觉使他们很多的作品看上去才华横溢,感觉非常后现代很自由很反传统,民族特征被唾弃,但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已经补回了这一课,因为美国人自己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现代房子连自己都不爱看,一到夏天就跑到欧洲满世界转悠。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不是想有就有的。
我读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天,看门的阿姨说有老乡来看我。来到接待室,我看见了他,他单肩靠着门框,双手插在裤兜里,一条洗得发白上面满是大兜的灰色粗布裤子,一件厚厚的暗咖啡色斜人纹双开衩休闲西装,里面是一件黑色套头高领的薄羊毛衫,脖子上挂着条深棕色围巾,鼻子上多了副细框眼镜。他看上去比那时高大了许多,样子显得自信而潇洒。"你长高了,公主"他满是微笑的眼睛看着我,有些幽默地说道。他的眼神清亮,很黑,镇定专注而平静自信。我喜欢观察人的眼,有的眼神飘忽不定,有的愚蠢自大,有的装模做样,有的空洞,有的狂妄,有的狡猾,有的猥琐……象他这种眼神,是非常少见的。"我明天带给你个盒子,你有空看看。"又听见他轻松地说道。第二天,我拿到了只盒子,里面全是信,一共有一千多封。我明白了,他原来每天都要给我写封信,整整写了三年多。有些信竟然写到了五线谱上,他说他将用爱情做音符,而这支曲子只有我能演奏;有些信是用颜料写成,笔触非常的美;有些信又是用漫画写成的,非常逗笑……这种创意和浪漫,我想任何女孩都是难以拒绝的,最后一封信是只粉色的信封,里面没有字,上面写着"这所有的信只是我给你的第一封情书和第一件礼物,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是的,他爱上了我,并且对我宠爱之至,让我感到十分甜蜜。他是令我无法挑剔的,无论从内在到外表,生活里也创意十足,极有品位,能不时听到他的作品获奖的消息,大五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工程,并有很多方案中标。建筑学界一个著名前辈,一直来信催促他报考他的研究生,但他却幽默地告诉我"我要早早毕业,为你挣大钱,娶你时呀,我要让你坐着白色大林肯兜遍上海,然后再带你去维也纳听音乐会,我要让人人都羡慕你。"这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实的肩膀,此时,我只想,你今后哪怕是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我也要嫁给你。我开始念大三时,他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电话,还得去我家,我毕业的时候,他烧的菜已经蛮水平的了。几年来,他明显地瘦了,做为男人,他负担太大。他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好几次,我深夜往他办公室打电话,听着他轻松而疲惫的口气,我都彻夜难眠。
我进入工作的第三的一个年头,他开始向我求婚,这一年29岁的他刚被提升为他们院最年轻的一个工程总负责人和一个科长。在单位集资的新房里,他做为社会男人的能力一目了然,里面该有的都有了,几乎都是最好的。他开室内设计公司的同学按我喜欢的方式进行的装修,看房子的时候,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你要是有半点不满意呀,他非再重新折腾不行,我可是没有象他这么宠过女友。是的,人生需要选择的地方并不多,我应该勇敢的选择婚姻,决定了,我要答应他,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决定呀!他出差去外地会审方案,除了开始几天,竟然没有电话给我。每次出差,他每天都要有电话给我的,我没有多想。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已经回来一星期多了,我略微有点吃惊。我一直沉浸在我幸福的决定之中,我愉快地告诉他,这周末等我的一个神秘电话。这是我七年来,第一次约会他并告诉了他我那绝妙的决定,我听得出来他高兴得都有些哽咽了。
出门前,父母告诉我:"孩子,就象爱自己一样爱他,幸福就会降临。"一路上,我反复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全部通通地告诉他,我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爱他,是多么的不能失去他;一定要告诉他,在我生命中他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无人能替;要告诉他,能做他的妻子我是何等荣幸,要告诉他,爱他就象爱我自己一样……
他坐在对面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我蓦然想起了十年前,我初三那个暑假,门口的那个同样局促和紧张的大男孩,是的,现在,我应该温柔的握着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去了趟洗手间,一刻钟后,他回来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我感到了有点异样。他突然显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你,我,她,"他艰难地支吾道。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我提醒自己要做到冷静。沉默了大约半小时,他不得不再次开口,"我,她,"他的额头上面密密麻麻有些汗光,那张英俊的脸痛苦地扭曲着,这张脸让我很难再看下去了,我默默看着桌上的水杯……"你就象个易碎的玻璃工艺品……我,我,是多么的爱你,"听到这里,我"恩"了一声清清嗓子,提醒他,现在他不一定有资格提及这个字。沉默,沉默又是沉默。听见他又虚弱的说道"她和我是一个单位的,是我工程组的……跟我同岁,外地人,一直非常主动。那天,北方的建设单位能喝,我被灌的一塌糊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她扶我回宾馆,她竟然没有走,都怪我一时糊涂……"……"……她拿着证明要我对她负责,我想给她一笔钱……可……"我天旋地转地紧紧盯着自己的手……发现它们根本陌生得就象是别人的手……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只要看定一样东西,就不会晕倒。我努力地想最后看一眼他,他的眼睛慌张得不知道该看
什么东西,却不敢看我,他的脸就只剩下一张不停张动着的嘴和一根不断蠕动着的舌头还有两排有些黄龋斑的牙,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
"你应该负责。"我轻轻的点头,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聒噪。这是这个晚上我讲的唯一一句话。我承认自己是个不合适宜的唯美主义者,是就是吧,至少我现在不想去改变它。
我拿起包走了出去,他急忙扑出来替我叫车,拉开车门,谦卑地立与一旁。
我自己叫好另一部车,顺利地回了家。
……,
他来家里找我,很是扰民,因为连我家里的小狗都不再喜欢见到他,最后家里的电话也换掉了。
我和我的父母出席了他的婚礼,因为据他未来的太太说若我们不参加,这婚礼就举行不了,我们一家看着他的准太太低声下气令人厌恶的百般讨饶,和她那已经再难以遮掩的隆起的腹部,同意了。他的婚礼非常简单,我所知道的新房已经买掉了,租了间旧房子,里面也没有收拾。不久,他的孩子降生了,竟叫了我的名字。
……
我开始生病,一病就是小半年,其中竟有两个多月在医院里爬不起来。
……
一年以后,我离开了上海,因为想要生活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