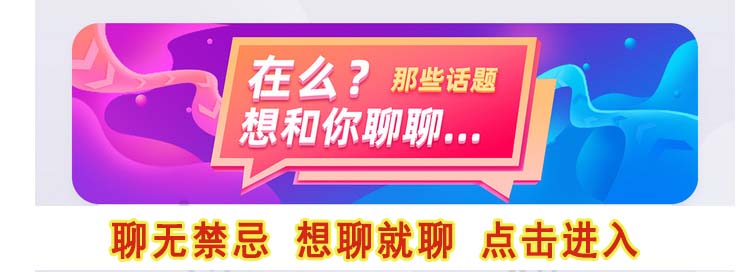不知为什么
刚刚还在水里吐泡泡的鱼
突然被摔到盆里
(灭顶的灾难总是突然而至)
洗鱼的家伙把袖子挽到膊肘上
水里包着刀子一遍遍的洗鱼
水妄图把鱼彻底洗干净
由里到外
鱼终于被洗干净了
被洗干净的鱼扔到了一边
张着嘴巴,瞪着无神的眼睛
如同一个傻子
洗鱼的水在盆里散发着鱼腥
像是满满一盆鱼的灵魂
鱼的梦境
鱼以外其它的一切东西
麦苗青青
绿了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呢?
这是公社的麦苗?
文化大革命的麦苗
麦苗青青
麦苗不乱占耕地
麦苗绿了汽车轮子
跑的飞快
绿了郊外加油站
停车加油
麦苗麦苗,怎么样
一片青青
看不到一丝成熟的痕迹
麦苗麦苗麦苗
连续叫上三遍以上
我像不像一只可怜的小羊
现在生活的地方曾是一片大海
现在的白天和黑夜在海面起落
那是一个贵夫人寂寞的年代·
贵夫人病了
贵夫人的病就是无止的时光
她的钻戒敲出木头一样的声音
她愈发的瘦了
她说出了爱着的人
被贬为了平民
她走进了医院
踏上了归路
她背后的花园与阁楼
与时间一样的速度倒塌
我现在胸前的饰物
曾经是她雪亮的牙齿
我现在的白天黑夜在海面升起
我曾经告诉过你
他是多么乖顺
(和我一样)
只咬突然的闯入者
像我一样爱着家人的裤脚
亲爱的,不知你忘了没有
连同我房子的地址
如果你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急得直跺脚
如果你快要认为我是个骗子
只要打听邻家狗的颜色
我就坐在那家相同颜色的窗帘后面
剪指甲
一张白纸承受肮脏的能力为0
一朵春天之花承受肮脏的能力
为全部
那是缘自一种深深的爱
应当还女人以清白
在没有世界以前
甚至没有梦想
也没有重力以前的样子
应当把爱都给孩子
追赶他们到孕妇腹内
一直到如一根两头光滑的棒捶
有时真想做一块石头
有坚硬的外壳
也有坚硬的内心
承受肮脏的秘密
连自己也不知道
一个母亲她真是太弱小与单薄了
她存在着
提着篮子穿过人流去买菜
后又默默回到家里掩上门
她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却有着两个庞然大物的儿子
一个大个子篮球运动员
在场上使万人呼叫
一个大胖子公司老板
掌管着一座大厦与一群员工
我们的想象到一个小小子宫
孕育两个生命为止
其它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其它的事情我们难以想象
一个那么单薄弱小的女人
如何产生出这样两个庞然大物
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
那家伙把这家伙的脑袋上敲了一个洞
于是这家伙以百分之百的速度冲向医院
脑袋上的洞目前正毫不犹豫的坚决的无情
的
流出这家伙身体里的鲜血
不管这家伙正以百分之百的速度冲向医院
脑袋上的洞总能以相同的速度流出鲜红的
鲜血
因此这家伙在奔向医院的路上
血迹没有一点间隔
你这家伙已经完蛋了
现在你真的应该安静的原地躺下
想想那家伙的样子想想生命存在着的幸福
时光
度过这珍贵的生命最后一刻
但你这该死的家伙坚持
以百分之百的速度奔向医院
值班护士喊来值班医生
值班医生叫来了主治大夫
等这帮家伙齐了
你已躺在医院墙角流尽身体里的最后一滴
血
这时候脑袋上的洞已经没有血可以流了
因此成了一个黑乎乎的洞
这时这帮家伙围着黑乎乎的洞
看到了你身体里的肠、胃、五脏六腑
这时你身体里的肠、胃、五脏六腑透过这个
黑乎乎的洞
看到了一圈脑袋及医院雪白的墙壁
脑袋上的洞像天窗一样
第一次射进了这个世界的光芒
她叫左慧
左右的“左”
智慧的“慧”
我们有时叫她“左”
声音洪亮清脆
仿佛回到文革时期
又仿佛她是
穿着绿军装的美丽姑娘
或者有时叫她“慧”
声音一样洪亮清脆
仿佛回到八十年代
在理想主义的温情时刻
这个名字熠熠生辉
当然我们通常还是叫她“左慧”
这时声音略微低缓
但依然生动活泼
洋溢着灵气
让人联想到“秀外慧中”之类
美好的形容词
并且让人进一步想到
她之所以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定是因为她叫“左慧”的缘故
她之所以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中
还能“扑哧”“扑哧”的
不断笑出声来
就像鱼儿吐出自由自在的水泡
一定也是因为
她叫“左慧”的缘故
那么她在这个
枯燥无聊的排版打字车间
已经工作了整整五年
难道也是因为她叫“左慧”的缘故吗
而当她好不容易脱下车间里的白大褂
换上的却是一套
暗黑色的西装制服
她站在工厂门口
活象一口陈旧的黑匣子在等候认领
这难道也是
因为她叫“左慧”的缘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