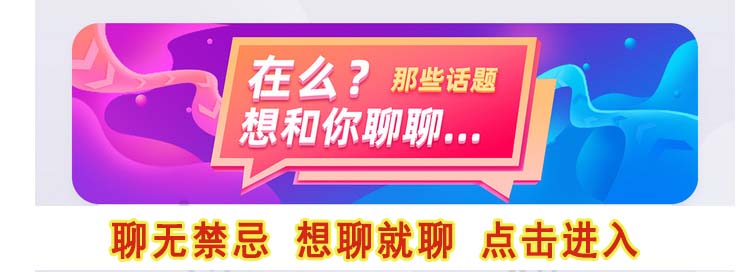我想生一儿子
是为了
心理需要
我的体内
开着另类的花瓣
使我觉得妙不可言
我在怀孕前三月
做好准备
查阅生育指南
把清宫预测生男生女表
一一翻遍
并且要丈夫配合
三月之内
在诸多方面
按部就班
可真是难啊
丈夫有时不快
某方面破坏了他的习惯情绪
自然不佳
我说
一切为了儿子啊
别想那么多
只想你白白胖胖的儿子就在
你的面前
叁月的时间
丈夫吃够了
菠菜 番茄 牛肉 鸡肉鱼和蛋
我吃土豆 豆腐 花菜 面包 莴笋和海带
播种的日子
是一个 平淡的夜晚
只记得是个朋友的生日
大家乐乐呵呵
心情都不错
十月之后
我果然生出一个儿子
告诉亲友 我的办法
大都很吃惊
其实这是控制的问题和关键
叁月的时间
能做哪样不能做哪样
能吃哪样不能吃哪样
都应该有控制
没有控制
就生不出儿子
没有控制
也能生出儿子
只是 运气好点
别告诉我
苹果上有洞
它早晨还新鲜
午后
温度
虚妄速度的爱情
让苹果
从内部
开始发热
苹果是苹果
这是你说的
苹果有苹果的生活
苹果有苹果的气味
一半有红
一半有绿
不明不暗的凹处
顺蒂而进
在深处的里面
啊呀
那么多的不同
门一关上
我只闻出味道
却难以
说出所见
这是一种
苹果的日子
即使变软
即使腐烂
也从 最新鲜的部分
开始
所以你说
我看不见青苹果 红苹果
它们有它们的秘密
而我有我的生活
2000.5.21
一个阶段
他有一个房间
没有干枝
没有
新鲜的东西
出现
他说
是我冬天的房间
屋外有水龙头
楼梯上来 有
四层
60秒不到
我的屋顶宽敞
太阳照得我
想飞
一个阶段
他有一个房间
有了枝叶
有了
叶上的一点东西
出现
他说
是我白天的房间
屋外有床垫
人顺楼而上
喘口气
看看上空
有没有什么
下来
一个阶段
他有一个房间
没有灯
四周的白墙
很白
他说
是我夜晚的房间
人在里面
鞋子丢了
会不会
看不见
一个阶段
他有一个房间
有过什么
落过什么
他想不起
他说
是我一个人的房间
只要站在原地
我动或不动
都没有人
发现
只是风吹来的一种味道
让我鼻子发酸
发酸
2000.5.18
我听见音乐
只有音乐
音乐的声音很响
在屋子里
飞着一般
整整一个下午
音乐都在
听着的人
只是两个
一个画画在左边的房间
一个写诗在右边的房间
其实只有音乐
只能有音乐
像这样
穿过无数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
一样飞着
画画的人画画
写诗的人写诗
多少年了
他们各在
不同的房间
2000.6.21
然后在这样的夜里
我还是想写
一个人和一个夜
我们分不清哪个执着
我们得在沉默中
把暗号和语言交换
我们得说
得在不经意中把隐私披露
我们得活着
得在老了的时候
把早年的幽默细细琢磨
我闪得为彼此
洁身自好
我们得中庸和平和
得把落花和落叶收集起来
掺进被污染了的空气和河水
我们得迂回曲折
得在命令面前说是
良心面前说非
得懂得内方外圆地呈现自己
我们得写
在夜里
一个人和一支笔
我们得留下些痕迹
表明我们曾掘土为食
自己养活过自己
夜风穿窗而来
我在等待什么
如果我有一双聋子的耳朵
或许我能听到那些逝去了的事物
它们在晨昏里唱歌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
瘦成了婴孩的人
他使我想到爱滋病
也使我想到生命的期限与债务
它使我不敢笑
也不敢说话
使我不想再把别人的恼怒放在心上
有一些东西我将永远不会领悟
旁观是我的债务
有一些联系出自我的不懂
回答是我的期限
每当我打开或熄灭自己
我都想叫出你的名字
称呼你的爱情
用了多久的时光我把自己堆起,
又用了多么慢长的时间一天天拆除,
直到无形。这就是一个生命能有的
全部辎重,上面甚至没有一行标记
表明你曾来到。看过。忧伤。
然后死去--
今晚我要写
伟大的诗篇
伟大之所以必要 刻不容缓
是因为我的渺小
三十八年
再没有可以重活的时光
我要和这滨海之城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的
GDP赛跑了
我要一个人
超过20万官员 外商 白领和群氓
我要象飞毛腿一样
抵达一个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终点站
然后在返身时
披挂着满身无人过问的诗篇
对你们点头 微笑 鞠躬 问好
依然如傻瓜一样纯洁
依然象傻瓜一样美好
头发越掉越少
我想好了
等到“全裸”时
我就去买个假头套
买个十八岁姑娘的外表
去大街上招摇撞骗
去陌生的远方开辟梦想
让假头套替我逍遥快乐
让假头套替我神魂颠倒
让假头套替我去挣钞票
让假头套替我应付填表
而真的我
秘密坚守一个秃女的谦卑与骄傲
看完黄色录象
庄老板叫我
一起去推土机那边坐
他掏出两支烟
给我一支
我给他点火
他吸着了
我等他说话
他又摸出一支
用烟头接燃
看我快吸完了
再递给我一支
我用烟头点上
因为无风
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
我没问老庄
他说我妈死去两天了
山丘无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