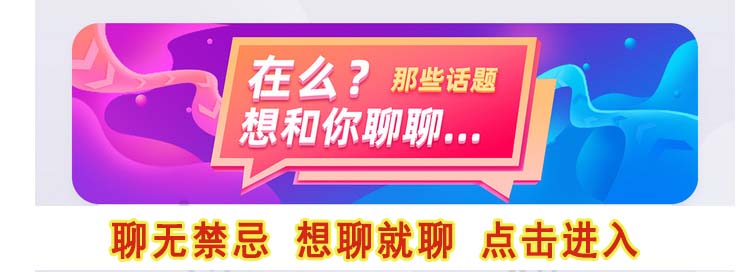从不同的角度
看到的总是这些
不知名的东西
它们掉在路边
它们毫无变化
但它们变化着周围的环境
它们变化着我们的心情
当我们冲到这里
总要停足
当我们还没有冲到这里
总要预算着与它们的距离
为了这些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面面相觑
犹疑不定
摸不清它们的底细
到底我们离不开它们
还是它们过分坚强
使我们暂时迷失方向
或者永远找不到任何一个方向
1991.4.3
站在或俯在树冠上
向下描述一棵梧桐的生长
只是在宽大的叶子反面
抹上各种花样的图案
薄得只有头发那样细的锯条
切下树皮的几百分之一
细心地研究细胞的组成
看看它几万年来的历史
在乡下的小学里爬上
斜长在校园里的梧桐树干
几个小子光着屁股
幸运儿在枝桠上哇哇地喊叫
1991.1.30
男孩和女孩
像他们的父母那样
在拔草
男孩的姑妈朝脸上擦粉
女孩正哀悼一只猫
有时候
他停下来
看手背
也看看自己的脚跟
那些草
一直到她的膝盖
如果不让它们枯掉
谁来除害虫
男孩和女孩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
1988
在我劳动的地方
我对每棵庄稼
都斤斤计较
人们看见我
在自己的田园里
劳动,直到天黑
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
黑暗早把它吓坏了
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
因为在我的田地
我习惯天黑后
再坚持一会儿
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
回家
留下那片土地
黑暗中显得惨白
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
它要照耀我的生命
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
陌生得成为它
饥腹的果物
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
“也许会有新的变化”
我怀着绝望的期冀
任由那最后的夜潮
拍打我的田园
1991
独自一人
在明亮的天光下干活
难道不比一群人更强
不伤害任何一种想法
他除去植物部分(据说有毒)
而另一些被普遍接受
天光明晰如缕
也像正午散落田头的麻雀
划分不同的地块
短尾巴的动物是贼
暴露给愁闷的芋艿
风移动,它们告辞
又离去不远
而种子跳跃着敞开明亮的天光
它们过夜的地方也是星光埋葬的地方
一个人劳动,手臂会粗壮
目光会萎缩
土地里跳出的石头有真正的冰凉
寒冷也会逐渐减弱天光
而当它增强一千倍
我见到一棵巨大的松树
劳动之余,我走向它
大地啊,你的子夜是否也这般安谧
而幸福的天光照明
六十岁,我还能这样
安睡如饴
1992
五岁的时候
父亲带我去集市
他指给我看一条大河
我第一次认识了 北凌河
船头上站着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
十五岁以后
我经常坐在北凌河边
河水依然没有变样
现在我三十一岁了
那河上鸟仍在飞
草仍在岸边出生、枯灭
尘埃飘落在河水里
像那船上的孩子
只是河水依然没有改变
我必将一年比一年衰老
不变的只是河水
鸟仍在飞
草仍在生长
我爱的人
会和我一样老去
失去的仅仅是一切白昼、黑夜
永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
1996
看见我的女儿满地爬
愉快地喊出“爸——爸——爸”
我多想成为她的弟弟而不是父亲
我多想在地上爬一圈
也围着我的脚跟
我没有成就感,整日里郁郁寡欢
人前笑容可掬,人后牙根痒痒
就让我作只小球吧
让我的女儿越拍越高
或者做只小鞋
穿在她脚上满世界走
我,一个孤独的男人
对什么都不信任
却在尘世留下这唯一的骨肉
好在你只要吃要喝而不要求灵魂
那就让我们作无腿的先生和女士
满世界爬吧
或者是夜风中感光的物质
漂在水上、空中……
1995
我看见田野里一把被遗忘的工具
为了能够找到我,我走向田野
这是一个发明事物极限而组成的黄昏
天空那么宁静
为了再次找到
那触怒土地后
尚未分类的躯体:工具
那把锈蚀的铁锹
紧咬着一条细窄的田埂
正如我目前所见的最佳方式
就是禁闭自我
随后而来的,蚕食铁锹的雨水
而形成一个自我独自留在外面
无人问津
我为我所见的事物
现身